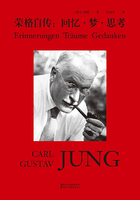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9章 中小学时光(6)
有了植物,神界在尘世就显得直言不讳,似乎有人窥探满以为无人注意的造物主,看他如何制作玩具或装饰品。与此相比,人与“道地的”动物是独立了的上帝粒子,因此,它们可以依己之愿游走或选择居住地。植物界则受制于其生长地的兴衰,它不仅表现出神界之美,而且表达出神界的想法,不抱什么企图,没有背离。尤其是树木神秘莫测,让我觉得直接体现了生命令人费解的意义。因而,人在森林里最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深意和骇人的影响。
我了解哥特式大教堂时,增强了此印象。但宇宙与混沌、意义与无意义、无主体的意向与机械规律性无穷无尽,于此隐藏在石头中。石头含有关于存在的深不可测的奥秘,它本身也是关于存在的深不可测的奥秘,是精神的化身。我暗中觉得这正是与我与石头相近之处:死者与生者中都有神性。
我已经说过,自己当时不可能以直观的方式表述感情与推测,因为它们发生于二号人格中,而我积极领会的自我——头号人格表现被动,属于往昔的“老人”范围。很奇怪,我不假思索地遇到他,体会了他的影响,他在场时,头号人格就暗淡得不复存在,而日益与头号人格同一的自我掌控场面时,如果确实想得起来,“老人”就是遥远而不真实的梦境。
十六到十九岁,两难困境的云雾慢慢散去,抑郁的心情由此好转,头号人格益发清晰地凸显。学校与城市生活占有我的精力,增多的知识也逐渐穿透或者压抑了预兆不祥的灵感世界。我开始系统地关注意识到的问题,所以,阅读了哲学史小引,由此概观了一切已经想到之事。我满意地发现,自己的许多灵感在历史上有相似者。虽然苏格拉底式的论据冗长,我还是特别喜爱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的看法,它们如画廊一般美丽而有学究气,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在爱克哈特大师身上,我才感到生活气息,虽然不会完全理解他。基督教经院哲学让我无动于衷,而圣·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唯理智论让我觉得比沙漠更无生气,心想,他们都想用逻辑绝招强求未曾领受而且也并非确知的事。他们意欲在的确涉及经验之处给自己证明信仰!我觉得他们如同只道听途说有像却不曾眼见之人。他们就试图用论据证明,出于逻辑原因,必定有这些动物,它们必定天生如此。我起先接受不了18世纪的批判哲学,原因容易理解。黑格尔吓退我是因为他的语言既狂妄又艰涩,我以不加掩饰的怀疑审视这种语言,觉得他仿佛一个人锁在自己的字词大厦里,还神情骄傲地在自己的监狱里散步。
我所做探索的重大发现却是叔本华,他是首个言说世界痛苦者,它显而易见、纠缠不休地包围我们,他言说迷乱、激情、恶,其他人好像都几乎不重视恶,总想把它化解在和谐与情有可原中。在此情况下,总算有人有勇气洞见到,世界根基情况不妙。他既不言说创世天意大慈大悲、大贤大智,亦不言说受造者的和谐,而是说明,充满痛苦的人类历史进程和自然的残酷性基于一个错误,也就是创世意志的盲目性。我觉得自己早先的观察印证了这点,我观察到鱼得病、奄奄一息,狐狸一身癞皮,鸟冻馁而死,鲜花点缀的草地掩盖了无情悲剧:蚯蚓受蚂蚁折磨而死,昆虫相互撕扯成碎片,诸如此类。但即使在人身上的经验教给我的也完全不是相信人本善、有德性。我太了解自己了,知道本人与动物可以说只是程度有异。
我毫无异议地赞同的是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悲惨描摹,而非他解决问题之道。我肯定,他说的“意志”实指上帝——造物主,并且说上帝是“盲目”的。因为我凭经验知道,上帝不受渎神的言辞伤害,相反,甚至可能要求有这种言辞,为的是不仅感觉人的光明、积极面,而且感觉人的阴暗与抗神,所以,叔本华的见解并未引起我的异议,我认为它是经事实辨明的判断。但更令人失望的是他的想法,即为了促使盲目意志逆转,智力只需给盲目意志递上上帝的画像。因为意志确实是盲目的,它怎么能看到这幅画像呢?即使它能够看到画像,为何就会由此说动它逆转呢?因为画像会给它展示的恰是它确实所愿之事。而什么是智力呢?它是人类灵魂的功能,并非镜鉴,而是无穷小的小镜,孩童把它对着太阳,期待反射阳光。我觉得这完全不恰当,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叔本华怎么会想到此类理念。
这促使我更透彻地研究他,他与康德的关系让人印象日益深刻。因而,我开始阅读康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为此颇费思量。我的努力有所值,因为自己相信发现了叔本华体系的根本错误,他犯了死罪,做了形而上学的陈述,也就是把一个单纯本体(nooumenon)、“物自体”实体化并加以认定,这得之于康德的认识论,对我而言,后者或许意味着比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更大的点拨。
这种哲学上的提高从十七岁一直持续至学医岁月,它的后果是我对世界与生活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我以前羞怯、胆小、多疑、苍白、瘦削,身体好像时好时坏,现在在任何方面都胃口大开。我知道要想什么,就动手去取,显然也变得更易接近、更健谈了。我发现,贫穷并非短处,远非痛苦的主因,跟衣衫褴褛的穷小子相比,富家子弟绝不占上风,幸福与否的原因比零用钱的多寡深刻得多。我比之前结交了更多好友,感觉脚下更踏实,甚至有勇气坦率言说我的想法,但很快得知,这却是令自己后悔不已的误解。我不仅遭遇诧异或者嘲讽,而且遇到怀恨拒绝。令人最为惊讶、不快的是,发现某些人视为我牛皮大王、“活宝”。连以前的骗子嫌疑也再现了,即使形式略微不同。又是一道作文题激起我兴趣,因此,我特别上心地写了作文,细致入微地推敲文笔,结果令人沮丧。老师说,“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绝对出色,但如探囊取物,看得出花在上面的认真劲和气力多么少。荣格,我可以告诉你,你这样轻率,过不了日子。生活就需要严肃、认真、用功、努力。你看看D的文章,他没你出色,但他诚实、认真、勤奋,这是生活成功之道。”
我的挫败不像第一次那么深重,因为虽然情非得已,老师对我的作文还是印象深刻,至少没有断言我剽窃。我虽然对他的指责提出抗议,但用来打发我的话是:“根据《诗艺》(Ars Poetica),虽然觉察不到成诗之难的那首诗最佳,但你的作文不是这种情况。你蒙不了我,它只是草率、不费气力地一挥而就的。”我知道,文中有一些妙绪,却根本不入老师的法眼。
此事虽使我恼怒,但同学中的怀疑对我分量更重,因为它们恐怕要把我抛回先前的孤立与抑郁。因什么而招致如此诬蔑,我伤透脑筋,小心打探后得知,别人不相信我,是因为自己常常信口发表议论,或者提及据说我确实根本不可能知晓的事物,比如据说我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对康德和叔本华略懂一二,或者对学校里的确根本“不会有”的古生物学略有所知。这些惊人的结论向我表明,其实所有迫切的问题都不属于日常生活,而是如我的高度秘密一样属于神界,最好闭口不谈。
从那时起,我避免在同学中提及这种“玄学”;在成人中,我不知可以与谁交谈而不必担心别人以为我是牛皮大王或者骗子。身上有两个世界相隔,我尝试结束这种分离,却受阻而停滞不前,感觉最为尴尬。一再出现的事件逼迫我脱离自己习惯的日常生活而进入无边无际的“神界”。
“神界”这个说法在某些人耳中听起来多愁善感,对我而言,绝无此特性。属于“神界”的是一切“超人之事”、耀眼之光、昏暗的深渊、无垠的时空中情感淡漠、非理性的偶然世界中极其怪诞之事。“上帝”对我来说是一切,不过并非使人升华。
四
年纪越大,父母和其他人就越发频繁地询问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此,我一片茫然。兴趣把我引向四方,一方面,自然科学以其基于事实的真知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与比较宗教史相关的一切都让人入迷,前者中有动物学、古生物学与地理学,后者中有希腊—罗马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我主要对它们感兴趣。当时却不知,对迥异学科的这种选择多么符合自己的双重天性,在自然科学中,满足我的是具体事实连同其历史初级阶段;在宗教学中,令人满意的是连哲学也探讨的精神难题。在前者中,我惦念的是感官因素,在后者中是经验。自然科学高度符合头号人格的精神需要,对二号人格而言,精神科学学科及历史学科则意味着舒适地上了生动一课。
在此矛盾情形中,我长久找不到头绪。我注意到,大舅不知不觉地把神学推到我身旁,他是家母家族中的老大,是巴塞尔市圣阿尔班区的牧师,在家族中有“小铁人”的诨名。没有逃过他眼睛的是:他跟都是神学家的几个儿子讨论专业问题,我听他们席间谈话时,专注程度何等非同寻常。我完全不能肯定,究竟是否有神学家与高不可攀的大学关系密切,因而比家父更有学问。但从这些席间谈话中,我从未感觉他们研究实际经验,甚至研究如我那类经验,而是只讨论关于圣经记述的学术见解,因为圣经记述关于奇迹的讲述数量众多、不甚可信,让我觉得极其不适。
上文理中学期间,我不仅为每周四都可以在这个舅舅家吃午饭而感谢他,而且为了绝无仅有的一项好处:可以偶然在他家饭桌上听到成年人睿智而理智的谈话。竟有这等好事,对我是重要的经历,因为周遭从未听人谈论学术内容。虽然向家父提出过要求,遭遇的却是令我不解的不耐烦和忐忑不安的抵触。几年后我才明白,可怜的家父不可以思考,因为怀疑撕裂了他内心。他逃避自我,坚持盲目信仰,不得不争得盲目信仰,想要竭尽全力地强求它,所以,不可能把它作为圣宠来领受。
舅舅和我的表兄们心平气和地讨论关于教义的学术观点,范围从教父直至最新神学,在肯定理所当然的世界秩序上显得有理有据。不过,其中根本未出现尼采的名字;而说到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的名字时,只勉强有肯定之意,称布尔克哈特“自由化”“思想过于自由”,这就暗指他对万物永恒秩序的看法有点剑走偏锋。据我所知,舅舅完全不知我多么疏远神学,我很抱歉不得不令他失望,但当时从不敢吐露我的问题,因为太清楚由此会对我产生多么不可预见的灾难。我的确两手空空,无以自卫。相反,头号人格坚定地使我尚属寥寥的自然科学知识有所长进,它们完全浸淫在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中。费力牵制头号人格的只是历史课成绩单和我周围似乎无人能懂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那几个神学家以称赞的口吻提及康德,不过,他的原理只应用于对手的立场,却不用于自己的立场,我对此也一声不吭。
所以,我跟舅舅全家坐在桌旁时,越来越不自在,习惯性地良心不安,周四成了倒霉的日子。在这个社会安定、精神泰然的世界上,我越来越觉得无以为家,虽则渴望偶尔降下激励精神的雨露。我觉得自己不诚实、堕落,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对,你是个骗子,你撒谎,蒙骗那些对你的确一片好意者。确实不能怪罪他们的是,他们居住在一个社会和精神安稳的世界里,对贫穷一无所知,他们的宗教同时也是有酬职业,他们显然不会考虑上帝如何能够使人脱离自己井然有序的精神世界,并惩罚人去渎神。我不可能对他们解释这些,如果解释就得身背渎神的污点,不得不学着忍辱负重,然而至今不算成功。
我身上的道德冲突加剧,带来的后果是,自己觉得二号人格日益可疑、难受,对这一事实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我试着消除二号人格,但就是不成功,虽然可以在学校里、在同学在场时忘掉它,在学习自然科学时,它也从我身上消失,但一旦独自在家或在大自然里,叔本华和康德还有厉害的“神界”又强势回归,我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含在其中,给这幅巨画填充色彩和形象。但作为小插曲,头号人格及为选择职业而操心在19世纪90年代隐没不现,我从历代岁月中徜徉归来时,它们就又出现了,令人沮丧。我亦即头号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迟早要确定愿意选择何种职业。
家父严肃地跟我谈了几次,我可以上大学学点什么,但若在乎他的劝告,那最好别学神学。“你什么都可以当,就是别当神学家!”当时,我们之间已经有一种默契,某些事可说可做,但不表态,比如,他从不质问我为何对做礼拜能逃则逃、不再参加圣餐。我越远离教堂,就越轻松。我惋惜的只是管风琴和圣歌,但一点都不惦念“团契”,对它根本想象不出什么,因为我觉得,出于习惯定期上教堂者,相互的“联系”还少于“俗人”,后者不那么一本正经,但那些人可爱得多,感情朴实,更加随和、快活、热情、诚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