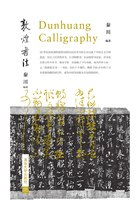
序言
Preface
刘正成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没想到,由酒泉电视台制作的《敦煌书法》在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播出后,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从书法艺术史学的视角看敦煌宝藏,它既是学术的,又是艺术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让国人颇有刮目之感。说它是学术的,是指它的现代艺术史方法论特征;说它是艺术的,则是指它丰富生动的影像视觉形象。
大家知道,“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一百年来的显学,但“敦煌学”中的书法艺术学却并不显,还有些冷落。王国维与陈寅恪二位先哲早就论述过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后的学术意义,至今仍是当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论箴言。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于是列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简牍等为证。陈寅恪又专就敦煌发现的材料立说,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如果就其学术史的源流和宏观影响来看,敦煌宝藏的发现,可以比肩1788年法国拿破仑的军官在埃及亚历山大罗塞塔城堡中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意义。由于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与破译,世界得以建立了“埃及学”;同样,由于1907年敦煌宝藏被斯坦因带回英国,世界得以建立了“汉学”。后来“汉学”内容拓展,便有了“敦煌学”。但“汉学”与“敦煌学”并非中国固有的学问,它和“埃及学”一样,均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的解读。“埃及学”“汉学”“敦煌学”均是“东方学”的分支。作为中国首任敦煌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季羡林先生则委婉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正因为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观,他们把敦煌宝藏中的写经与文书只看成是文献,所以英国人把敦煌写经和文书从大英博物馆分出来,放进了大英图书馆,而把敦煌绘画则留在了大英博物馆。大约在他们眼中,绘画是艺术,写经与文书则不是艺术。因之,“敦煌学”中没有书法艺术学,便合乎其逻辑。可以理解,西方人能识汉字已属不易,要看懂书法则是难上加难了。像贡布里希这些后世学问家,虽然也声称书法是艺术,而且热爱书法艺术,但终归望难止步,对中国的书法艺术只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敦煌学”中关于书法艺术研究的部分,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人的肩上。
“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形、音、义、美是汉字的四重属性。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5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汉字书体发展历史的参照。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与各个时代的写经、写本,均是极为宝贵的碑拓和墨迹珍品,它们来自中原南北各地,因之也是中古时期书法艺术风格发展的历史缩影。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这部《敦煌书法》纪录片还从社会风俗学的视角,用“上大人孔乙己”的写经生认字练书墨迹,举证了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艺术学习和创作的状态,让这些宝藏与时代和生活获得了密切关系。换句话说,这部专题片让一段辉煌书法时代“活”了起来。其中,关于东汉末年“草圣”张芝及其兄弟张昶的内容,也让汉魏时期书法史“活”了起来。我认为,这是使用影像资料进行“敦煌学”研究的一篇“论文”。现在,将之集辑成书,便具有这种敦煌书法研究的文献形态,让“敦煌学”的艺术研究获得了多维度效应。同时,作为当代书法史研究来说,也是开了新生面。
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敦煌书法》并非一个考古学的知识片,它还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现象对接,呈现了知识的立体感和当下感。也许因为该片制作人本来就是书法家的缘故,影片通过与当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对话,探讨敦煌书法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影响力,这似乎已超出传统“敦煌学”的藩篱,把它的触角伸向了更远更深的地方,避免了静态历史知识可能的平板和枯燥。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中国符号大大增多,并接上一百年来国际“敦煌学”的潮流与文脉,使之推向新的高潮,达到新的水平。那时,我们是否可以把季羡林先生的那句话修改一下骄傲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感谢酒泉电视台的《敦煌书法》节目制作人,感谢参与《敦煌书法》节目的所有学人、艺术家和同人!广大读者在欣赏影视听图像后,手执此书,必将进一步感受到你们创造性的劳动与弥足珍贵的贡献。
聊献数语,是为序。
庚寅孟夏匆草于泥龟梦蝶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