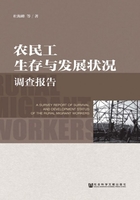
第一节 教育
教育是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核心指标,是个人能力快速增长和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户口居民在教育程度上普遍低于非农业户口,这与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制度不均衡等密切相关。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教育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户籍带来的教育差异在农民工身上逐渐发生变化。
一 总体状况
本次调查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的分布如图3-1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多处于初中水平(占38.85%),其次为高中(或中专、技校),占30.62%,大专及以上比例为22.8%,而小学及以下比例最低,为7.74%。全国“六普”数据同一年龄段的人口中,以初中水平为最多(占48.08%),小学及以下比例为21.41%,高中(或中专)占18.57%,大专及以上比例为11.93%。比较二者发现,本次调查农民工的总体受教育水平高于全国人口,尤其接受高等教育和高中(或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这意味着在西安市打工的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

图3-1 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
此外,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以初中水平为最多(占61.1%),其次为高中(或中专),占17.7%,小学及以下比例为15.9%,而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最少,仅为5.3%。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本次调查中在西安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更高,尤其高中及以上比例已经超过全国农民工1倍以上。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西安市的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有相对优势。
对不同年龄的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教育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本次调查数据显示,46岁以上农民工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77.27%),高中(或中专、技校)学历为19.32%,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3.41%。4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3-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近年来,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在年轻一代中所占比重显著升高。1978年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分水岭,在此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即35岁及以下的两个年龄组的农民工60%以上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在5%以下。
表3-1 按年龄划分的总体受教育状况

近年来受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的影响,年轻农民工中接受过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如26~35岁的农民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是36~45岁的7倍以上。与之相仿,受过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也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36~45岁的农民工接受过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比46岁以上的多了4个百分点以上,26~35岁的农民工接受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比36~45岁的多了7个百分点以上,16~25岁的农民工接受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比26~35岁的多了5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本次调查还发现,16~25岁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滑。这很可能是因为,16~25岁正处于求学的年龄,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仍然在学校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这群人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故使得本次调查结果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此外,这种现象也可能和他们幼年的留守、随迁经历有关,这种特殊的经历很可能导致他们与普通未成年人在接受教育上存在差异。因此,必须开始对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目前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予以关注。
二 结构特征
(一)代次差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制度日益完善,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教育机会上存在着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第一代农民工高。本次调查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第一代农民工仍然是以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为主(占66.58%),受过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已经占据一定的比例(占24.87%),而受过大专及以上的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仅为8.54%);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比第一代提高了近9个百分点,受过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比重得到了跨越性的提升,是第一代比例的3倍多(见图3-2)。这足以证明两代农民工的教育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也意味着教育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农民工群体中已经初见成效,同时为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图3-2 农民工按代次划分的受教育水平
(二)性别差异
一直以来,我国教育就存在着较为突出的性别差异,在农村更甚。由于受到性别偏好、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一般低于男性。然而本次调查发现,女性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男性农民工,受过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高出4.54个百分点,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农民工也比男性农民工高出5.33个百分点,只有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比例略高(见图3-3),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并不完全一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图3-3 农民工分性别受教育水平
为了进一步分析男女农民工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将代次视角纳入后发现,无论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均高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男女农民工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在受过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上,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高出5.44个百分点,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高出3.46个百分点;在受过大专及以上的高等教育上,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高出4.54个百分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则比男性农民工仅高出1.91个百分点。在受到本科及以上的更高等的教育中,男性始终比女性的比例更高,且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性别差异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见图3-4)。

图3-4 农民工分代次和分性别教育水平
教育性别差异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广泛推行以及高等教育的进步。然而本次调查发现的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性别差异的异常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男高女低”的教育现状得到改变或者缓解,这很可能是由外出务工行为的特殊性导致的。
(三)地区差异
除了在年龄和性别方面存在差异以外,我国教育一直以来也呈现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东部地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然而本次调查发现,来自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接受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最高;东部地区次之;来自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见图3-5)。

图3-5 农民工分地区教育水平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纳入代次视角进行比较发现,两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明显缩小,尤其是大专教育在中西部有了明显的提升,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的比例差异在各地区之间开始缩小。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比例来说,来自东部的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低于来自中西部的第一代农民工,而三个地区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已经发生变化,来自中西部农民工的比例开始低于东部;从受过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情况来看,来自东部的第一代农民工低于来自中西部的第一代农民工,而来自东部的新生代农民工远高于来自中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来看,来自东部的第一代农民工远高于来自中西部的第一代农民工,而来自中西部与来自东部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著降低(见图3-6)。出现这一结果很有可能与本次调查所在地有关,在西部中心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来自本省或附近省份的,而精英农民工更可能选择近距离流动,但是这种地区间差异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教育发展水平逐渐趋于均衡。

图3-6 农民工分代次和分地区受教育水平
三 代际传递
教育的代际传递是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已经成为代际继承或流动的中介,是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社会上层会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教育代际传递关注的是教育如何从父辈传递到子辈的过程,在这个传递过程中拥有较高文化教育程度的父母,对子女会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也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进而子女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一)代际传递的总体水平
从父代受教育程度与子代受教育程度的比较来看,子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代。在父代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重约为35%,而高中及以上的仅为22%;与之相比,在子代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7.74%,而高中及以上的已经达到53.42%(见图3-7)。

图3-7 父亲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比较
从农民工父代到子代的教育代际传递中发现,子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总体高于父代,且相当规模的父子受教育程度较为接近,也就是说对角线上或附近向上的数值较大。例如,父亲受教育程度为不识字,那么子女处于不识字和小学水平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父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其子女也处于初中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明显更高,处于其相近教育程度如高中的比例也较高,而处于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仅为6.42%。这一特征同样存在于父亲处于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中(见表3-2)。由此可以看出,若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则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通常也会较高,且父亲与子女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传递效应。
表3-2 按父亲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子女受教育状况分布

以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基点,子女不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绝大多数都位于父亲受教育水平基点附近。例如,不识字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水平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为96.03%,但其中超过一半[(23.81%+46.03%)/96.03%=72.73%]的子女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初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水平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为92.53%,其中超过一半(50%/92.53%=54.04%)的子女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的农民工,虽然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已经提升,但是总体上还是偏低的。当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时,其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为62.01%,其中超过一半的子女都接受了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34.92%/62.01%=56.31%),而向下流动的比例为3.35%。与之相似,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处于高中及以上的,其子女向下流动的比例为19.89%,而其中又以初中为主,约占向下流动总数的89.49%(17.80%/19.89%=89.49%)。
综上所述,农民工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教育传承现象,父辈的教育水平越高,子辈的教育水平也会随之升高。
(二)父亲打工经历与教育代际传递
外出打工与教育存在着天然联系,选择打工很可能意味着接受教育的停止。由于子代对父代的传承是多方面的,父代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会对子代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会给予子代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子代沿着父代的打工经历放弃接受教育而出去打工。本次调查发现,父亲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更高(见图3-8),父亲的打工经历会显著降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

图3-8 按父亲打工经历划分的子女受教育状况分布
从教育的代际传递上看,父亲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父代与子代的代际传递负向效应比没有打工经历的更为明显;而父亲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其父子受教育程度向上流动的比例也更大。例如,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且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教育代际传递向上流动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且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高了2.32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则比其低了1.09个百分点。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且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向上流动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且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高出19.24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的则低了1.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父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且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向下流动比父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且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低了14.36个百分点。
从代际传递的向上流动来看,父亲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教育代际传递向上流动的总体比例约为51.64%[(35×100%+92×90.21%+166×42.77%)/366=51.64%],而父亲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教育代际传递向上流动的总体比例约为59.36%[(126×96.03%+174×92.53%+358×62.01%)/849=59.36%],父亲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比父亲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低了近6个百分点(见表3-3)。
表3-3 按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打工经历划分的子女受教育状况分布

(三)父亲的党员身份与教育代际传递
家庭的政治背景是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父亲的党员身份常作为家庭政治背景的代理变量进行测量,很多研究结果表明父亲是党员的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更高。本次调查发现,父亲是党员的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父亲不是党员的。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来看,父亲是党员的农民工不论是大专还是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均明显高于父亲不是党员的;从仅接受了初中以下教育的情况来看,父亲是党员的农民工处于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比例明显低于父亲不是党员的。然而,在接受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农民工中,父亲不是党员的农民工所占比例略高(见图3-9)。

图3-9 按父亲党员身份划分的子女受教育状况分布
从代际传递上看,父亲是党员的农民工教育代际传递向上流动的比例明显低于父亲不是党员的;而向下流动的比例略高于父亲不是党员的。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父代的政治资本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在减弱,但这一结果也可能受到样本规模的影响。从代际传递的向上流动来看,父亲是党员的农民工教育向上流动的总体比例约为39.20%[(12×100%+29×86.21%+65×63.08%)/799=39.20%],而父亲不是党员的向上流动的总体比例约为60.53%[(149×96.64%+237×92.41%+459×54.90%)/1016=60.53%]。从代际传递的向下流动来看,父亲是党员的农民工教育向下流动的总体比例为12.56%[(29×0%+65×1.54%+93×25.81%)/199=12.56%],而父亲不是党员的向下流动的总体比例约为5.81%[(237×0.42%+459×4.14%+171×22.80%)/1016=5.81%](见表3-4)。
表3-4 按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党员身份划分的子女受教育状况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