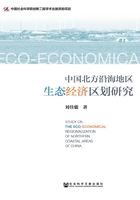
第二章 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 相关概念解析与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是生存于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交叉领域的边缘学科,它吸纳了地理学的地域分异规律、生态学的生态系统观和经济学的区位论等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研究是生态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生态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指导。本章对与生态经济区划产生、发展有紧密联系的几个概念和进行区划、模式研究时有重要作用的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对与生态经济区划密切相关的理论和区划进行梳理和评价,旨在为后面的工作奠定基础。
(一)相关概念解析
1.自然区划
自然区划主要依据客观自然地域的分异规律性所进行,主要反映自然区的客观实际,自然区内部具有相对一致性。自然环境的研究是生态学的重要内容,早期的生态区划实际上是自然区划,自然区划为现代生态区划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生态区划植根于自然区划,又不断发展和健全自然区划。
追溯自然区划的历史,可从19世纪初A.V.Humboldt绘制世界等温线图开始,至今已近200年。自然区划经历了区划理论的创立和手段、方法的不断更新,自然区划也不断发展并逐步独立。自然区划的发展过程是人类系统认识生态环境的过程,也是进一步进行农业区划、工业区划、经济区划、生态经济区划等的基础。
以近代地理学鼻祖Humboldt绘制世界等温线图为起始标志,到20世纪40年代,其间代表人物及主要贡献有:俄国学者Докучае(1899)的自然地带学说;美国学者Merriam(1898)的农业带学说;英国学者Herbertson的生态地域观点,Tansley(1935)的生态系统概念;德国学者Kopen(1931)的全球气候带;中国学者竺可桢于1931年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标志着中国现代自然区划的开始,随后黄秉维于20世纪40年代初首次对中国的植被进行了区划。20世纪50年代,在对中国自然资源深入调查及分析的基础上,自然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自然地域特点的区划原则和指标体系。其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完整的是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编写出版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它明确了区划的目的,拟定了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的区划原则和方法。与此同时,许多省区也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自然区划。20世纪80年代,各单项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更加趋于完善,相继有《中国植被》、《中国土壤》和《中国自然地理》等一系列著作出版。
这一期间自然区划的发展特点是:建立了自然区划的基本思想和体系框架,引入了生态区域的观点,进行了基本自然要素——气候和植被区划的实证研究,注重将自然区划的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其中,生态区观点的引入(Merriam,Herbertson,Tansley)为以后生态区划的发展和独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70年代,自然区划得到了蓬勃发展,其间主要特征是自然要素的区划研究逐渐丰富,除气候和植被区划被广泛研究并逐步细化外,土壤区划也得到了发展(侯学熠等,1956;马溶之等,1958)。同时,区划要素、区划指标体系的研究也逐步深入(Penman,1956;黄秉维,1962;李治武,1962;陈传康,1962),促进了综合自然区划的发展。这一期间,生态区域全球分异研究得到发展,如Holdridge(1967)研究生态带(Life Zone Ecology),Walter和Box(1976)进行了全球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分类等,促进了生态区划从自然区划中分离。
2.经济区划
经济区划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仅介绍中国经济区划的相关内容。
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区是以综合性大中城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具有全国性专门化职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组合单元。它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商品经济相当发达条件下社会劳动地域分工与协作的必然产物,具有客观性、阶段性、过渡性和综合性特征。经济区在实践上因社会经济各因子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变化而具有阶段演进性,在空间上因各经济区对外联系范围错综复杂而具有各经济区之间的界线重叠交错的过渡性,在职能上受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民族、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具有综合性(赵济、陈传康等,1999)。
经济区划在综合分析区划单元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和劳动力、技术、交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原则、生态原则、社会原则,突出各经济区在自然社会条件的区内统一性和区间差异性,以及区间经济结构的差异互补性和相互联系性。中国经济区划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区划一直采用“两分法”,即全国划分为沿海与内地。1954年建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经济协作区,1961年华中区与华南区合并为中南区,全国划分为六大经济协作区。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取向的稳步推进下,各种区域规划方案、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调控理论都先后被实施及运用,对全国各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生态区划
1976年,美国学者Beiley发表了《美国的生态区域》(Eco-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之后又于80年代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生态区域划分的文章(1983,1985,1989),成为生态区划与自然区划分离的标志。这期间,Rowe(1981)和Klijn(1994)探讨了景观生态分类(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的途径,Wiken(1982)研究了加拿大生态带(Eco-zones),Beiley研究了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态区划(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状况,Denton(1988)和Host(1996)探索了生态区划的定量方法,1996年Beiley发表了生态系统地理(Eco-system Geography),进一步促进了生态区划研究体系的完善。
中国生态区划研究的壮大与自然区划的发展相辅相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垂直分异的研究(郑度,1979,1985,1990,1999)和区划地带性理论(赵松乔,1983;席承藩,1984;黄秉维,1989;任美锷,1992;杨勤业等,1996)的深入探索使自然区划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实践领域也越来越广。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区划首先在农业领域展开研究(熊毅,1980,1981;傅伯杰,1985),1988年侯学熠发表了《中国自然生态区划与大农业发展战略》,是对这一时期农业生态区划的总结,也成为中国生态区划研究之始。1999年,傅伯杰发表了《中国生态区划的目的、任务及特点》,郑度发表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研究》,杨勤业等发表了《中国西部生态区划及其区域发展对策》和《中国生态区划方案》,成为国内生态区划研究与自然区划分离的标志。
4.生态经济区划
依据客观自然地理的分异规律性所进行的自然区划,主要停留在对自然表象的认识上,区划指标过于单一,不能满足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经济学思想的诞生以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发表作为标志。但真正结合经济社会命题开展生态学研究的,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她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详细揭示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和经济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此后,一批论述生态经济问题的著作相继问世,开始了生态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新时代,卡逊成为新的“生态经济学”时代的代表人。1976年日本学者坡本藤良的著作《生态经济学》出版,第一部生态经济学理论论著问世。之后各国生态学家陆续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包括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Goldsmith)的《生存的蓝图》,沃德·芭芭拉(W.Barbara)和杜博斯·雷内(D.Rene)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等。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及区域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越发符合世界发展的需要,得到普遍的关注,其地位也越来越高,各国生态学家对生态区划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并认识到纯自然生态区划的局限性,更加关注人类活动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地位,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功能的生态经济区划也应运而生。
在总结中国生态建设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环境学家马世骏教授于1981年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他指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其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功能、结构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是工农业布局、环境管理和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据,因而亦是进行农、林、牧、副、渔业生产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合理配置人口分布等问题的重要参考”(马世骏,1986)。王如松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城市和农村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纽带,由社会、经济与自然三个亚系统组成的相互作用与制约的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一基础上区域规划由单纯的自然生态分析向涉及自然、社会、经济诸多方面的综合分析转变,经济生态规划随之逐渐展开。1989年周纪伦等主持的上海郊区生态经济规划,以区域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为划分对象,构造了一个能反映城乡地区生态经济系统整体特征的框图模型,开了国内区域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先河。自此以后,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生态经济综合区划蓬勃开展起来。
5.主体功能区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其中,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国家发改委,2006)。
主体功能区思想来源于德国。德国不仅是国际公认的政府在空间秩序组织和空间规划领域走在前列、规划体系和制度保障也相对完善的国家,而且是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等经典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主要发源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为区域发展和空间布局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樊杰,2007)。
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主体功能区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区域的分工与合作,优化资源空间配置(陈潇潇,2006);引导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构建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优化区域开发秩序,实行空间管治(王东祥,2006);规范城市发展规模,形成合理空间开发结构,创新区域管理模式,分类管理和调控区域(张岩铭,2006);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考核标准,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邓玲,2006);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适应自然,逐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开发格局(樊杰,2007;高国力,2007)。
经过综合分析对比,本书认为,主体功能区指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划分主体功能区主要应考虑自然生态状况、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区位特征、环境容量、现有开发密度、经济结构特征、人口集聚状况、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等多种因素。
主体功能区规划直接以解决现实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为宗旨,尽管因理论和经验准备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从理念、目标取向和主要作用等方面综合审视,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一项尚未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及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空间规划实践(樊杰,2007)。
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有利于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绩效考评体系,加强和改善区域调控。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人口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建设规划等在空间上开发和布局的基本依据。
从自然区划、生态区划、经济区划、生态经济区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发生发展的历程看,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建立在自然区划、生态区划、经济区划和生态经济区划等基础上的综合性规划,具有更强的战略性和指导性。
(二)生态经济区划相关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是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容许的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生态经济区划的理论基础是地域分异规律、生态经济学理论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相关理论,本节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评价,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1.地理学地域分异理论
地域分异规律是地球表面的自然、人文景观及其组合按一定方向分异的规律,是不同尺度地表空间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区划研究的理论基础。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是其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
地域分异规律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由基本的地域分异因素派生出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形成了地表空间不同尺度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空间尺度可分为大、中、小规模或全球性、大陆性、区域性、地方性(和局地性)等层次(景贵和,1986;赵济、陈传康等,1999)。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地域结构层次之间,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高层次的地域分异规律是控制低层次地域分异的背景或外界因素,低层次的地域结构单元的分异排列关系是构成高层次地域分异的基础。地表景观的每个层次根据其具体的分异因素和相应的结构特点,完成特定的功能和体现各自的整体性特征。各景观地域之间按等级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体现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协同和共扼关系(赵济、陈传康等,1999)。其二,地球表面空间的任何区域都同时受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二者实际上是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既互不从属,也互不联系。因此,区划研究既能以地带性因素为指标,也能以非地带性因素为指标。
地域分异理论是区划工作最基础的理论之一。地表自然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一性推动了区划工作的进行。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各部分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之间的相互分化和由此产生的差异,形成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规律。自然地域分异研究强调综合观点,任何一个地域都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综合体,其形成都包括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要素、现代因素和历史因素、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尤其是受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结构和特点上的地域差异。人类生产活动的方式、方向和程度及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因地而异,导致不同地域生态经济的结构和功能、物质、能量、价值和信息的转换效率、流动方式和强度,以及派生的生态和经济的矛盾与调节系统稳定性的途径、手段和措施都有所不同。区域复合系统的生态经济特征与功能的差异性是进行区划的基础。生态经济地域复合体的划分与合并是对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空间层次和有序性的“刻画”过程。
无论是划分还是合并,都以地表自然-社会-经济地域体系的空间规律和有序性为依据,并且分别由相应的分异或集聚形式来体现。通过分析不同区域单元之间的生态功能和生态需求的差异性与同类生态区的相似性,通过合并或划分的方法,形成生态经济区划。根据城市群生态经济的地域差异性进行的综合区划,有利于科学调控整个系统,建立高效、和谐的区域生态经济系统。
(1)空间大尺度地域分异规律。
空间大尺度的生态经济地域分异规律包括自然要素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分异规律。自然要素的地域分异规律主要表现为自然景观的纬度地带性和经度地带性的规律性分异,辐射平衡与干燥度是形成该分异规律的主要因素。纬度地带性是热量自赤道向两极变化的表征,经度地带性是水分自海洋向内陆变化的指示。全球范围内地域分异规律主要是太阳能和地球内能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海陆分异和热力分异。大陆范围的地域分异主要表现为热量的纬向分异和干湿程度的经向分异,形成温度、降水、土壤、植被等要素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王传胜,2002)。
人类在人种、数量、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宏观尺度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人种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人数的纬度差异和经度差异,人类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等。John Luke Gallup等对世界人口的地域分异进行研究发现:世界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纬10度至北纬40度之间,即亚热带-温带的范围内;人口的分布趋于向沿海集中及自沿海向内陆呈带状递减的现象(尤其在欧亚大陆表现明显)。赵济和陈传康等(1999)研究发现瑗珲—腾冲线东南部分面积占全国的42.9%,却分布着全国95.4%的人口。
全国宏观尺度的经济活动亦体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农业经济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呈现比较明显的地带性规律,我国粗线条的农业经济活动分异特征可以概括为南稻北麦、东农西牧。农业部门结构、农作物品种和耕作制度与纬向热量、经向干湿度和大地貌的影响密切相关(周立三等,1989,1993)。而从经济总量上来看,Jonh Luke Gallup等(1999)发现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有类似的特征:GDP密度较高的地区,一是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二是在大陆连片分布的地区,从沿海向内陆,呈现依次递减的带性特征。我国全国范围的经济总量分布也具有这样的特征。2009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GDP总量比值为3.81∶1.43∶1。
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分异规律与全国自然气候条件、地貌分异规律高度一致,无论以瑗珲—腾冲线来划分还是以东、中、西三大地带来划分,都体现出了这一分异特征。
(2)空间中小尺度生态经济地域分异规律。
中小尺度的生态经济地域分异规律主要受中小尺度的自然气候条件、地形地貌、资源条件、区位条件影响。我国中小尺度的生态经济地域分异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生态环境地域分异决定了社会经济地域分异的基本格局。中国面积广大,南北差异、东西差异明显。中国的气象与气候、水文、土壤和植被分布的经度地带性和纬度地带性差异反映了我国东西部、南北方生态环境的显著差异。
从海陆分布看,我国位于全球最大陆地与最大海洋之间,因而季风气候显著,加上青藏高原的影响,季风气候更加明显,对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和地域差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东部海洋性湿润气候至西部大陆性干旱气候间的水平变化使得自然景观的经度方向的干湿带性差异颇为显著。我国的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气温分布总的特点是北冷南热,这决定了不同农业作物的种植区域。中国地理中水文要素也有明显的南北分异。在纬度、海陆位置和地形因素影响下,我国气候从西北向东南由干到湿,自北而南由冷到热,这样的水热分布规律,决定着我国土壤与风化的地球化学过程由西北向东南、由北向南逐渐加强。生态环境的地域分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分异特征。
第二,农业资源的地域组合决定着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农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是生态环境的直接反映。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发展水平,尤其是耕作业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影响人口分布、经济社会空间分异的最根本因素。目前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产业集中区基本上都集中于农业资源组合条件比较好的区域,这在西部反映得更明显,如关中平原、四川盆地、河西走廊、天山北麓等。
第三,能矿资源的地域组合及开发决定了能矿工业基地和矿业城镇的地域分异。能矿资源的地域组合及开发构成了城市地域分异的重要基础,甚至决定了有些工业基地和城镇的形成,这在西部地区反映得更加明显(董锁成等,2002)。例如,攀枝花、克拉玛依、白银、石河子、玉门、金昌、格尔木等多分布于重点资源开发区。这些地区尽管资源富集但区位较差、交通不便、远离市场、经济基础差,如三峡库区、陕甘宁接壤区、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攀西-六盘水等地区。由于有国家急需的重要资源,政策导向使这些地区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中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热点”地区,其交通状况和通达性也随之改善,发展潜力巨大,有望成为西部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第四,区位、劳动力、技术、市场、政策等要素的地域组合,决定着生态经济地域类型。以综合经济要素为指标的综合指数的分异特征,说明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要依赖本地区总体的状况,包括位置、自然条件、政策支持、地区内部发展差异等,这些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组合与生态环境要素叠加决定着生态经济地域类型。
总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地域分异上较高的相关性,导致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不相协调的矛盾十分尖锐,生态环境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强约束。我国社会经济在地域分异上较高的相关性反映了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对社会经济地域分异的深刻影响。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根据生态经济分异规律,对各地区进行生态经济区划,为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功能区形成奠定基础。
地域分异规律是不同尺度地表空间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区划研究的理论基础。北方沿海地区属于中小尺度的地域分异范畴,由于其地形复杂多样,既有水平地带性分异规律,也有垂直地带性分异规律,在对其进行生态经济区划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地带分异规律。地域分异规律不仅是自然区划、生态区划的理论基础,也是生态经济区划的理论基础和主要遵循的原则。在生态经济区划工作过程中,依据地域分异规律对研究区进行定性描述是十分必要的。
2.系统论
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并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要素是构成系统的最基本单位。系统结构指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的组合方式,是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秩序。系统功能则是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所反映的能力。一定的系统结构对应着一定的功能,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结构的改变必然引起系统功能的改变,功能对结构有反作用。环境是指存在于系统以外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总称。所有系统都是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运行的,系统必然要与外部环境产生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交换。依据系统论的观点,只有系统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相互协调,才能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
(1)复合系统协同论。
地球表层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城乡的工农业生产、各种经济活动和代谢过程是生存发展的活力和命脉;而人的社会行为及文化观念则是演替与进化的动力泵。系统应以物质能量的高效利用、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动态的自我调节为系统调控的目标。就区域复合系统而言,区域的地质构造、气候状况、水系结构、地貌形态、资源禀赋、周边环境等是长时段因子;区域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人口-资源结构等是中时段因子;区域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资源利用方式等是短时段因子。对于制约区域复合系统结构功能状态的长时段因子,只能适应,无法改变。我们只能通过调整中时段因子和改变短时段因子的状态来实现由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在对区域进行生态经济区划研究的过程中贯穿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协同进化原理和支配原理,能使区划工作始终贯穿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使区划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协调共生的原则,实施区划成果时能最大限度地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弱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990年,Norgaard提出了协调发展理论,认为通过反馈环在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可以实现共同发展。这一理论把经济发展过程看作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协调发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协调,它是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科技结构调整与量度变化的过程,是后一层面的基础。第二个层面是发展。它是在第一层面协调的基础上,对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结构、发展趋向和发展效益的导向。协调和发展始终处于互为推动的动态过程中。只有协调,才有发展,在协调发展运行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种思想在生态经济区划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生态经济区划是在生态与经济关系出现尖锐矛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是进行生态经济区划工作的主要目的。在区划研究中始终贯穿协调发展理论,对于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生态系统提供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并接受经济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实现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循环,因而成为生态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系统的发展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又对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调控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以及向生态系统排放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和能量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等;间接影响表现为经济系统的调控政策影响物质流和能量流而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环境效应,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
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维持依赖来自系统外部的物质和能量,以及系统运转过程中产生的价值流和信息流,而能量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价值转移和信息传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能量流成为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动态描述:来自地球外部的太阳能和少量太空物质进入地球表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并与来自地球内部的矿物质和化石燃料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而在这部分物质和能量的消耗过程中又产生大量无效物质和能量(如废弃物和能量的损失等),返回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又以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在农村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中流动,产生以能量流为驱动的价值流和信息流。
(2)热力学二定律与物质平衡理论。
热力学第二定律,也称熵定律。熵是不能做功的能量,也用来表示系统的无序或混乱状态。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物质-能量的使用导致能量从低熵的地方向高熵的地方单向流动,熵在增加,并从有序变得无序。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能量转换过程中,从一种能向另一种能的任何转换都不是完全有效的,有一部分能量将会以热的形式失散而失去潜在做功的能力,能量的品质不断降低,且能的消费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系统从有序渐渐变成无序,如果没有外界的能源投入,封闭系统最终会耗尽能量,进入没有任何变化的平衡态。
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关系受热力学二定律的约束。任何物质系统的质量都不会因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各种反应而增加或减少。人类从自然界中开采矿石、燃料、天然气和其他有机物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利用时,质量并没有改变。只要所有的投入不能全部转化成产出,生产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物质、能量残余物,而残余物的很大一部分又只能回到环境中去。如果残余物的排放超过一定限度,环境容量与自净能力就会日益减小。当废弃物的排放超出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所允许的范围时,就会导致环境污染。如果人类继续采用现行的经济运行方式,由经济增长而导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存在有限的低熵能源储备(化石燃料),这一系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减少能源,最终导致可用的能源消耗殆尽。然而,地球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地球从太阳那里直接获取能量,并具备有限地利用这种能量的能力。因此,生态系统能通过吸收低熵能量,将系统维持在高组织、低熵状态。
物质平衡的思想来自热力学二定律。20世纪60年代,鲍尔丁(Kenneth R.Boulding)发表了《即将到来的太空船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一文。他依据热力学定律,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环境经济学问题。他指出:“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生产和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其物质形态并没有消失,必然存在于物质系统之中,因此在设计和规划经济活动时,必须同时考虑环境吸纳废弃物的容量;虽然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对环境容量的压力,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断增加的熵意味着100%的回收利用是不可能的。”这一理论是物质平衡理论的萌芽。
20世纪70年代初期,科尼斯(Allen V.Kneese)、艾瑞斯(Roben U.Ayres)和德阿芝(Ralph C.D’Arge)依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物质平衡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物质平衡理论。主要思想为:一个现代经济系统由物质加工、能量转换、残余物处理和最终消费四个部门组成。这四个部门之间,以及由这四个部门组成的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流动关系。如果这个经济系统是封闭的(没有进口或出口),没有物质净积累,那么在一个时间段内,从经济系统排入自然环境的残余物大致等于从自然环境进入经济系统的物质量。这个结论的推论是:经济系统排放的残余物的数量大于生产过程利用的原材料数量。这种结论同样适用于一个开放的、有物质积累的现代经济系统,只是分析和计算更为复杂。现代经济系统中虽然越来越多地使用污染控制技术,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治理”污染物只是改变了特定污染物的存在形式,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污染物的物质实体。例如,治理气体污染物,使排放的气体变得清洁,但却留下了粉尘等固体污染物。这表明,各种残余物之间存在相互转化关系。为了使人类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减少经济系统对自然环境的污染,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物质及其能量的利用效率和循环使用率,由此减少自然资源的开采量和使用量,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
物质平衡的思想表明,采用末端处理模式进行污染物处理,并不能使污染物消失,只是改变了污染物存在的形式。当某种环境容量未被充分利用时,末端处理的方法才是有效的,否则,必然会造成某种形式的污染,而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相比之下,提高污染物循环利用水平和采用清洁生产,才是更有效的办法。
3.生态经济学理论
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和系统论为理论基础,模拟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要求经济活动效仿生态系统的结构原则和运行规律,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生态经济的核心是强调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强调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以来,生态经济学成为地理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出现大量影响深远的生态经济专著,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美国学者埃里克·爱克霍姆纪念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10周年的专著《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西蒙思(G.Simmons)的《最后的资源》等。生态经济专著及生态经济学家的活动对公众的环境意识产生了极大影响,促进了公众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并在促进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制定、推动环境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部分发达国家也开始设计使用含有生态指标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如NEW(经济净福利)和GSP(总可持续产品)等。
发展生态产业和产业生态化是实现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途径。生态产业(Ecological Industry)可理解为“生态化”的产业。所谓生态化,是指产业依据自然生态的有机循环原理建立发展模式,将不同类别的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关系,从而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促进物质循环利用,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产业生态化是指依据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外研究产业生态化问题较早,目前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生态化市场机制,其主要手段有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环境设计、绿色技术开发、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控制等。2000年后,国内研究逐渐增多,对生态产业与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转型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目标指向等进行了探讨,尤其近几年生态产业园区建设的实践研究增多,并涉及了区域内的产业循环系统。
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态经济学家更重视生态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深化,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中国的生态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于1980年提出并建立的,至今已经整整30年。许涤新倡导:“要加强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1980年9月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和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参加。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体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科学相结合的特点。
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是在国外有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经过许多学者在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调控等方面的深入探索与研究,最终形成了“生态经济系统”理论(中国生态经济学会,1992),并在生态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资源与环境物品的产权界定和有偿使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尝试。生态经济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全国生态环境损失的货币计量等。研究方法也逐渐趋向多元化,并与生态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方法相互借鉴,如徐中民等采用绿色国内生产净值的概念衡量了1995年张掖地区与水有关的生态环境损失,生态足迹方法在中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应用等。
董锁成和王海英(2003)分析了西部地区面临的生态恶化与加快发展的双重挑战,认为超常规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西部摆脱“脆弱-贫困”恶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他们提出了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战略途径。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战略:①依靠科技和市场的生态化、绿色化的农业产业化战略;②多元化超常规的生态工业化战略;③积极发展以旅游为主导的生态型第三产业。二是非均衡重点突破、分类指导的区域生态经济布局战略:①区域生产力宏观布局战略;②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生态经济模式;③集中力量建设一批西部生态产业带和生态产业基地;④走生态型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李宇和董锁成等(2004)通过分析定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主要制约因素,提出了甘肃省定西地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胡宝清和陈振宇等(2008)根据各个地区的生态经济状况,把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建设实践总结为恭城模式、毕节模式、平果模式、移民模式等10种主要模式,并选取广西都安县作为典型研究区,探讨西南喀斯特地区典型农村特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王如松(2005)认为,面向循环经济的产业生态转型就是要通过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改革去合理、系统、持续地开发、利用和保育生态资产,为社会提供高效和谐的生态服务,建立一种整体、和谐、公平、持续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秩序,而不只是急功近利地去追求产量、产值和利润,其宗旨是要促进从物到人、从链到环、从刚到柔、从量到序的转型。产业生态转型的途径包括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功能导向、结构柔化、区域耦合、社会整合、能力组合、增加就业、人性化生产。
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优化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目前,将产业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引入整个产业系统进行分析,研究产业生态化进程中的结构调整和优化问题尚不多见。而产业系统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本身就是产业生态化实现的一种方式,应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纳入产业生态化的体系中进行研究。应通过区域、行业间的耦合,将生产、流通、消费、生态服务和能力建设融为一体,实现废弃物交易、资源共享以及生态资产的正向积累。
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能值分析、生态足迹分析展开。
(1)能值分析理论。
能值分析方法的前身——生态能量学,被认为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能量关系及其能量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生物能量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是生态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祖元刚,1990)。能量生态学研究的是生态系统的能流与其他生态流(物质流、生物流、信息流等)等数量变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生态系统和复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传递、转化规律的科学(蓝盛芳等,2002)。
能量的流动和转化是任何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生命科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世纪中叶,作为研究能量相互转化过程中遵循的规律——热力学定律已经形成。1840年,J.P.Joule和J.P.Mayer通过大量实验证实了“热功当量”理论。1922年,A.J.Lotka提出了最大功率原则的思想,并提议作为热力学第四定律,H.T.Odum将“最大功率原则”(Maximum Power Principle)定义为:具有活力的系统,其设计组织方式必须能从外界获取可利用能量加以有效转换利用,并能反馈能量以获取更多的能量,以应存活之需。一个组织能够生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增长、再生产等多方式的较大能量输出,而且与它规模相关的高产出的组织可以在竞争中赢得生存。
由同一能量来源(太阳能)的能量,经过一系列转化而成为能量流动网络,H.T.Odum称之为能量链。它清楚表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转换,以及系统的等级关系。能量在系统能量链的每一传递、转化过程,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均有能量耗散流失。因此,随着能量由较低等级的生产者传至较高等级的消费者,其量越来越小。为了产生高等级的能量,必定消耗大量低等级的能量。随着能量从低级至高级流动、转化和传递,其数量越来越少,其能质越来越高。具较低能质的能量,如太阳能、风能、雨能等,经传递与转化而成为较高能质的能量,如生物能、化学能等,维持人类生存活动的需要。能质和能级越高的能量,就需要越多的太阳能转化,太阳能值转换率由低到高随着能质和能级的提高而逐渐增大。能值转换率则是衡量能质的标准。任何能量转化过程都是由很多焦耳的低等级能量转化成很少焦耳的另一种高等级的能量。某种能量的转换率越高,表明该种能量的能质越高,即在能量系统中的等级阶层越高。大多数系统的能量传递与转化随着能量的减少,能质和能量转换率逐渐增高。
1984年,H.T.Odum基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特征以及热力学定律,提出了以能量为核心的系统分析方法——能值分析法,该方法能够定量地分析生态承载力的现状。1986年,Vitousek等对初级生产量的人类占用进行了研究。1992~1996年,Rees和Wakemagle提出和完善了生态足迹方法,并对52个国家以及全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在合适的情况下,最大功率产出是多种系统生存的标准,换句话说,“适者生存”这一说法可以用“单位时间内工作效率最高的系统将会生存下来”来解释。Charles A.S.Hall(2004)这样评价最大功率原则:“Odum留给我们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中,最能改变我们如何理解地球的一个就是最大功率原则。这个理论的框架改变了我们理解生态系统、自然选择甚至是我们的环境的方式。这个概念虽不总是最适合的,但却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具有指导性的定义。”直至20世纪50年代,H.T.Odum又对生态系统的能量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概念和理论观点,其中包括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能量系统(Energy System)、能质(Energy Quality)、能质链(Energy Quality Chain)、体现能(Embodied Energy)、能量转换率及信息等观点。这是第一次将能流、信息流和经济流联系在一起,生态系统中的这几个功能过程不再是孤立的了。而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能值”和“太阳能值转换率”等一系列概念,则将对能量的分析发展到了对能值的研究,将能流、物流、货币流及其他生态流进行了有机结合,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广泛应用。
(2)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足迹”也称“生态占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模型是通过测定一定区域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消费量以及吸纳人类产生的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面积大小,与给定的一定人口的区域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pacity)进行比较,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它的值越高,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就越严重。生态足迹的意义在于探讨人类持续依赖自然以及要怎么做才能保障地球的承受力,进而支持人类未来的生存。
国际上关于生态足迹的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诸多有生态经济学研究背景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Odum E.P.(1975,1989)探讨了一个城市在能量意义上的额外的“影子面积”(Shadow Areas),Vitousek P.等(1986)测算了人类利用自然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Jasson A.M.(1978)等分析了波罗的海哥特兰岛海岸渔业的海洋生态系统面积,Hartwick J. M.(1990)提出了绿色净国家产品(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概念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等在1992年提出生态足迹概念,并由Wackernagel等加以完善,发展为生态足迹模型。其后,与生态足迹模型测度目标相类似的研究还有:F.E.Europe(1995)提出的环境空间(Environmental Space),Pearce D.W.等(1993)提出的真实储蓄(Genuine Savings),De Groot(1992)、Costanza等(1997)、Turner(1991,1998,1999,2000)等提出的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等。然而,生态足迹分析与“真实储蓄”等方法不同,对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指示意义也不相同,其寻求从生态与经济两个角度与层面来探讨对可持续发展的测度。
生态足迹概念作为可持续发展定量方法的一种,于2000年之后引入中国,曾被翻译为生态基区,也被翻译为生态占用、生态痕迹、生态脚印、生态空间占用等。生态足迹一方面体现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持能力,应用较广。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应用滞后4~5年,应用方向主要集中于全国尺度以及各类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度量,其他方面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
4.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国际环境委员会于1978年正式提出,其定义的提出则推迟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被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1991年Pearce根据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处理的不同,将可持续发展能力分为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两大类,这可以视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中,反映弱可持续性的指标包括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和真实发展过程(GPI),反映强可持续性的指标包括生态足迹,此后还出现了美国资源环境经济整合账户体系(SEEA)、日本广义资源环境账户体系理论框架(CSEEA)等。近年来,西方生态经济学家更重视对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和所谓“全球问题”的研究,如可持续发展的衡量、自然资产的估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经济政策的建立与管理等。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系统发展观,是当今世界认为最能有效解决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视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以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强调各成分之间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的发展,是人口、经济、环境之间相互协调的发展,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后代人利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遵循持续性原则(生态、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公平性原则(代内横向公平、代际的公平)、协调性原则(人口、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发展)、共同性原则(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
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多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第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视角。该视角的研究多以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以资源环境保护与永续利用、生态循环平衡等作为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生态平衡、自然保护、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合理开发与永续利用等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问题,其焦点是力图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这一视角的基本观点为:生态环境资源是除人口之外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维护生态和经济系统的恢复性,即寻求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视角。该视角的研究多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国际及区域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调整与优化、要素供需均衡为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研究区域开发、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资源供需平衡等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其焦点是力图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扣除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率的差额”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这一视角的基本观点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增长对资源基础的压力,从而增强增长的可持续程度,体现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性作用。
第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视角。该视角的研究多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发展、公平分配、利益均衡和代际公平等作为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研究人口增长与人口控制、消除贫困、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利益均衡和科技进步等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其焦点是力图把“在经济效益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的公正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这也是该视角的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和伦理准则。这一视角的基本观点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消除贫困、公平分配物质财富、资源合理配置、科技进步、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和健康发展的社会,也是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人口与环境相互依存的社会。
第四,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论视角。该视角的研究多以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复合系统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性、协调性和持续性等作为基本研究内容,以系统论为基础,吸收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模拟技术、管理科学和决策论等科学理论,以系统动力学的方法,依因果联系建立系统的结构模型,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边界、系统环境、系统要素、系统结构与功能、系统发展机制和系统约束等可持续发展中的系统性问题,其焦点是力图把“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逻辑自洽”作为衡量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这一视角的基本观点为“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三者的和谐动态均衡是人地复杂巨系统保持良好的可持续性的集中体现,通过对复合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影响和控制,使其在可持续的方向上达到“良性循环”,相互之间可以“协调发展”,从而达到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主要基于承载力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展开。
(1)承载力理论。
可持续发展指标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就是承载力理论。1838年,Verhust第一个将相关理论用逻辑方程表示出来,并将其命名为容纳能力,作为反映环境约束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的指标,这可以说是近代研究承载力的起源。1921年Park和Burgess提出承载力的概念,将承载力定义为“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越发严峻,承载力的研究重点开始快速转向环境对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限制,用来说明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根据上述对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的概念界定,可以将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解为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和一定时期内,在保持区域资源总量和结构满足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区域环境维持稳态效应能力没有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区域内资源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综合支持能力。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的实质,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利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区域资源环境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持和承受能力进行客观描绘和度量。
在研究区域承载力及承载状况的过程中,区域系统是由人类及其活动、资源、环境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系统中,任何两个子要素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多反馈、多回路、循环流向的网络关系。由于这种网络关系的存在,各承载体之间存在“相互广义可替代性”[1]。由于区域生态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际交流使得各种承载体能够相互补充,所以在考虑以物质基础为主要决定因素的支撑能力时,交通等交流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的科技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然而全球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却日益显现并尖锐。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对承载力的研究呈现多种研究方法并举、各种要素承载力共存的局面。人类对承载力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科学准确地度量承载力,进而判断人类的发展状况。因此,对“承载力”这一概念的政治价值的讨论以及对其评价方法和应用领域的不满更是激发了学术界对承载力理论和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的热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土地承载力的研究。爱丁堡大学的Malcolm Sleeser教授提出了用于计算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ECCO(Enhancement of Carrying Capacity Options)模型。Lieth 提出了净第一性生产力计算模型,并对全球生态系统净第一性生产力进行了计算,间接度量了承载力。1996年,美国在南部佛罗里达州门罗县人口最多的地区——佛罗里达可斯地区设立了一个重点承载力研究项目,即“佛罗里达承载力研究”。虽然这个项目与南部佛罗里达州耗资78亿美元恢复城郊湿地生态系统的计划相比,在地理尺度、资金投入和预期研究时间上要小,但是该研究项目在把承载力概念应用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中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掀起一个研究承载力的热潮。1999年Harris和Kennedy建立了一个用于全球农业产量的逻辑斯谛模型。基于该模型,预测了21世纪的全球农业的供给和需求,暗示世界的发展与农业承载力密切相关。
国内全面展开承载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土地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等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86年由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等多家科研单位联合开展的“中国土地生产潜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项目,是迄今为止中国进行的最全面的土地承载力方面的研究。彭再德等(1996)对上海市浦东新区进行了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研究。余丹林等提出用于区域承载力评价的状态空间法,并将之应用于北方沿海区域的承载力研究中。高吉喜(2001)提出了生态承载力AHP综合评价法,并对黑河流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评价。
(2)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并称为21世纪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实践模式,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整合与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基于循环生态原理并按系统工程方法组织的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及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的网络型和进化型复合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反馈式流程,以代替传统经济的“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的线性单向流动型经济,而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的建立依赖以“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核心的行为原则,即减少污染物产生是循环经济流程的首要目标,包括采用减少原料使用量、制造工艺再设计等方式实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而对于不能削减但可以利用的废弃物应保证加以回收,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最终对不能循环利用的废弃物需进行无害化处置。
循环经济理念从根本上拓展了人们对于资源范畴的认识。首先,传统意义上对环境产生严重危害的废弃物在循环经济理念下将得到社会的再认识,不可利用的污染物质将转变为世界上唯一在不断增加的潜在资源,把废弃物资源纳入循环经济体系既可保护生态环境,又增加了社会占有的资源和财富,缓解资源短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废弃物资源化过程改变了人们的资源价值观,由传统的“资源无价”观念改变为“资源有偿使用”观念,促使人们利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过程。
循环经济理念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宇宙飞船经济观》一文中提出,污染物质是未得到合理利用的“资源剩余”,应以能够循环利用各种物质的循环经济模式代替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可有效解决污染问题。循环经济理念提出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基本停留在理念阶段,相关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较少,人们对生产过程的认识局限于产业链模式,对污染物的管理则局限于“末端治理”层面,缺少以市场手段为主的污染控制模式,也没有意识到污染物源头控制和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污染物的对策视点转移到前端垃圾的减量措施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有的国家以立法等方式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也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响应。例如,德国1996年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处置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使用-最终处置”;日本也在2000年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境保护法规,如《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等,形成较为完善的循环型法律体系。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也进行了循环经济的生产实践,主要从企业内部的循环、企业之间的循环和社会循环三个层面进行。企业内部循环的典型案例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的循环经济模式,体现为企业内部各生产工序之间的原料循环利用和废料再加工后循环利用。企业之间循环的典型案例是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即在园区内建立以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生产厂为主体的企业群,形成能够进行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交换的工业企业共生体,进行废气、废水、废物和废热的贸易和再利用。社会循环的典型案例是德国的双轨制回收系统(DSD)模式,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发展旧物调剂和资源回收产业,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
中国也在循环经济理念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的应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包括在工业领域推行清洁生产,开展不同区域和行业的试点与示范,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如广西贵港、广东南海)、生态城市(如长春市、沈阳市等),以及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省建设和循环经济省建设等。理论研究方面,广大学者除了积极呼吁进行循环经济建设,探讨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之外,还就循环经济理念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城市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做了探讨,但付诸实施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