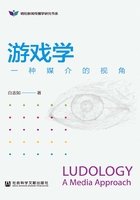
第一节 游戏的功能
首先,游戏能够满足人们对自由、自足、轻松、快乐的追求。“许多人认为过分关注游戏的后果将会破坏游戏的一个重要属性,即游戏是为了游戏而游戏,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用这一属性来界定玩耍,它将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如果玩耍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玩耍的目的就在于玩耍的过程之中。这样的话很难将赌博归入玩耍。例如,如果中了彩票获得几百万英镑的话,我们怎么还能将它看成是在‘玩耍’呢?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克劳伊斯等早期作家将玩耍本身当成目的,并非因为其自成体系而是因为其非生产性的特征。这样的话,彩票获奖就可以被定义为玩耍,因为‘玩’彩票并不需要生产而只是重新分配金钱而已。将赌博界定为玩耍的这一定义方法显然忽视了游戏者对其参与游戏活动时所赋予的价值。如果我们考虑到游戏者的动机和方法的话,玩彩票仍然符合玩耍自成一体这一标准。购买彩票可能仅仅是为了享受这一过程。如果参与者的目的是需要或想要赢得大奖,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话,玩耍的独立性、自愿性和娱乐性显然就有问题。”[1]在这里,游戏是和现实生活并行而不交叉的一条独立的线索,人们沿着这条线获得的是无关功利的自由、自足。
其次,游戏具有传播和沟通的功能,是维系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纽带。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之“游戏——人的延伸”[2]这一小节中,用14页的笔墨阐释了游戏。他认为:“游戏是我们心灵生活的喜剧模式”,游戏是众人参与的“一架机器”,游戏是“群体知觉的延伸”,游戏是“社会肢体的延伸”,游戏是“传播媒介”。其中,麦克卢汉论述了橄榄球优于棒球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因为棒球这种运动是每次只做一种动作的运动,球员的位置固定,他们被分派的专一职能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分派专门职能的做法,是属于正在消失的机械时代的;机械时代的被分割的任务、人员和行业都属于管理组织之中。由于电视形象本身是新型的、团体参与性的、电力时代的生活方式,所以它养成统一知觉和相互社会依存的习惯。这就使我们与棒球的独特风格产生了疏远;棒球的独特风格,是偏重专门分工和注重球员位置。文化变迁时,体育运动随之而变。棒球变成了工业社会争分夺秒生活的优雅而抽象的形象,所以过了10年新型的电视时期以后,它就失去了适合新型生活方式的心理相关性和社会相关性。这种球被逐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已经转向美国生活的边缘地区了”;“与此相对,美式橄榄球不固定阵式,任何球员或全体球员都可以在球赛中转换为任何一种角色。因此,目前它在普遍受欢迎的程度上正在取代棒球,它非常符合电力时代非集中化的团队游戏的新式行为”[3]。游戏为人们服务,能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游戏才能够生存下来,否则,便被人们冷落和淘汰。因为:“正如我们的口语一样,一切游戏都是人际交往的媒介,除非成为我们内心生活的延伸,否则它们是既不能生存也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手握一块网球拍或13张牌,那就是同意在一个人为构想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动态机制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最喜欢那些模拟自己工作和社会生活情景的游戏,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难道我们喜欢的游戏,不正是给自己提供了一种超乎社会机器垄断暴政的一种解脱吗?一句话,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思想——既是模拟表演又是持续压力的解脱——不正是完美地解释了各种游戏、舞蹈和欢乐吗?嬉耍和游戏要受人欢迎,就必须传达提倡生活的回声。另外,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游戏,就等于堕入了无意识的、行尸走肉般的昏迷状态。艺术和游戏使我们与常规惯例中的物质压力拉开距离,使我们去做这样的观察和询问。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的游戏,给一切人提供了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直接手段,任何单一的角色或工作,都不能给任何人提供这样一种直接的手段。所以,所谓‘职业’体育运动是自相矛盾的。当通向自由生活的游戏之门导向专门的职业时,人人都觉得是不合适的。”[4] 这是游戏和竞技保持边界的必然选择,回归生活才能让每一个人得益于游戏,而不是被不断标准化和社会化,因此游戏是保持人类个体多样性的一种渠道,最终整体上形成一个民族的特色。
所以,“一个民族的游戏解释了有关他们的许多情况。游戏是像迪士尼乐园的一种人为的天堂,或者是一种乌托邦似的幻景,我们借助这种幻景去阐释和补足日常生活的意义。我们在游戏中设计出非专门化的手段,去参加当代广阔的戏剧生活。然而,对文明人而言,参与的观念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抹去个人直觉界限的深度参与他是体会不到的,印度教的‘得福’(darshan)就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参与,这是一种大群人对肉体存在所做的一种神奇体验”[5]。如果游戏是替代性满足,那么是心理层次上对现实的反抗或者逃避,还是一种积极的调和手段,也可能兼而有之,但与胡伊青加致力于在文化中寻找游戏成分就有所不同,因为这样的游戏显然带有更多的消费和产业色彩,这不仅是文化工业的问题,而且是媒介渗透的问题,因此麦克卢汉在这里是把游戏作为一种人体延伸,他没有论及更为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或者文化传统,而是强调游戏的替代性与社交性功能,而且是在大众媒介崛起的年代。
“任何游戏,正像任何信息媒介一样,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它对群体或个人的影响,是使群体或个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实现重构。一件艺术品除了它对观赏者产生的影响之外,别无其他存在或功能。与游戏或大众艺术、传播媒介一样,艺术能使人的社群形成新的关系和姿态,它有力量借此将自己的假设强加于人”[6];“游戏是延伸,但不是我们个体的延伸,而是我们社会肢体的延伸。游戏是传播媒介。这两点现在应该清楚了。如果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游戏是大众传播媒介吗?’回答也只能是:‘是的。’游戏是人为设计的情景,旨在容许很多人同时参与他们自己团体生活中某种有意义的模式。”[7] 所以在麦克卢汉这里,游戏并不是人们生活的“隐匿”,而是人们内心的“延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维系,游戏都扮演着如“媒介”一样的角色,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再次,游戏具有政治、经济功能,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在中西方历史中,游戏与国家兴衰相连,多数与其政治功能有关。这一点在印度板球发展的历史中已经比较明确,因为板球游戏不仅仅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游戏,而且是关涉国际关系与权力和文化殖民的游戏。在中国古代,游戏发挥政治功能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游戏不仅仅可以是个人晋升仕途的途径,也是国家巩固统治、进行外交或者发动战争的方式。游戏在古代也具有商业功能,这一点并不逊色于今天的社会。因此毫无疑问,从古至今,游戏都可以作为一种产业或者社会发展晴雨表而存在。例如,19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闲暇消遣娱乐方式也随之变化。因为经济萧条,人们无力支付高昂消费,因此诸如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俱乐部等在1934年前后减少了一半;但是人们开始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廉价消费品中,活动也从室外转向了室内,例如拼图、跳棋、国际象棋等,而且一档“业余爱好大厅”的广播节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各种酒馆、旅店、游乐场、俱乐部等开始设置弹球游戏机、赌博机等游戏机。“1938年11月所做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股票市场之外,全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承认,在过去一年里曾沉迷于一种形式的游戏赌博,三分之一的人光顾过教堂的抽奖,四分之一的人玩过抽彩盘,类似数量的人玩过读博机,五分之一的人玩过赌钱的扑克牌……据推算,20世纪30年代晚期,各类游戏装置每年要吞掉5亿到7.5亿美元。这些家庭类游戏和公共场所游戏机的兴起,为电子游戏的出现开拓了广阔的消费市场。”[8]这其实可以称为“口红效应”,即在经济萧条年代人们对于廉价消费品的热衷度明显上升,而不为人关注的是,游戏在这种历史情境中恰恰是大众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政治、经济的晴雨表。
最后,游戏具有传承文化、缔构文化的功能。例如,游戏的文化功能之一表现在游戏和文学作品的关系上。《东京梦华录·卷五之京瓦伎艺》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延叟,《孟子书》……杨望京,小作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刘百禽,弄虫蚁。”[9]其中还记载了傀儡戏、教坊舞蹈等。另外,游戏的文化功能也表现在风俗习惯中。例如,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之卷二十《熙朝乐事》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10]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游戏成为其中的必需品。游戏不仅表现文化,而且能够生成文化,因此游戏的文化功能也表现在文化价值的缔构中。游戏在其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例如可以是个人能力的表现、男女定情之物,或者是武器发明以及技术文明等。总之,游戏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例如游戏的规则、游戏的服装、游戏的工具和场地、游戏的组织以及游戏迷亚文化等,都是其文化价值的体现。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玩牌戏的时候,参与者“又唱竹林戏,讴歌逸兴赊”[11]。这种“唱牌之癖”形成了麻将参与者的自我“文化圈层”,外行人是听不明白的;参与者可以分享这种“契约”,具有认同感和自足感。因此,胡伊青加认为:“游戏是一种必需,游戏推动文化,或它在实际上的确成了文化。”[12]这种反映文化和生成文化的特征使游戏自身的价值得以巩固和延续,也提升了游戏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