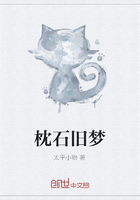
第16章 玄纶悠游长安景 知府智破花银案
昨日说到泰安和茂财把这“十”字头上加了一小撇成了个“千”字,登时就把“五十两”改作了“五千两”。这也怪玄纶不小心,要是写作“拾”字,料是神仙也没法动手脚了。可是玄纶终是个镇日读书的公子哥儿,哪里懂得这些门道,这回可是找了奸人的道了。泰安对茂财道:“你且把这账目圆一圆,回家躲几天,等把这位尊神送走了再来。”茂财笑道:“如此,就仰仗掌柜的周全了。”两人是一跟绳子上的蚂蚱,泰安自然尽心尽力,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玄纶虽然憋了一肚子火,然而既是出门游玩,见此关中景致,就把这些烦心事儿一概抛在脑后了。长安城里有一座有名的大慈恩寺,寺中有一座大雁塔极是耸构巍峨,气度非凡。话说唐朝玄奘法师从天竺取经东归后,便将经卷与佛骨舍利都藏于此塔地宫之中,每至夜半,寺僧常闻塔内隐隐有诵经之声。多方找寻,而塔内空无一人,细细审听,声自地宫出,以有千颗佛舍利之故也。后慈恩寺屡遭兵火,而大雁塔独存至今,众人无不以为此乃神灵佑护之功也。唐代中进士者,都要到大雁塔下赏景饮宴,并赋诗言志。玄纶来到塔下,见有许多题跋,中有白乐天一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意气风发,何等雄壮,至于中年贬谪江州,仅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便令人扼腕叹息无尽。《贺新郎》词云:
快意平生志,十余年、焚膏继晷,搏来今日。
玉带方巾高踏马,人报鸿胪传炙。
频换盏,觥筹交隙。
斗笔舒文三千字,笑请君、留作香山集。
离别后,恐难悉。
功名岂在千钟秩,问何方、民风疾苦,吾其将适。
不得家家丰粮米,誓断归鸿消息。
未敢悔,一生浪迹。
且趁少年斟美酒,过今宵、各路他乡驿。
行道远,不劳忆。
玄纶观之咨嗟不已,叹道:“乐天文才盖世,直到二十七岁才中进士,且仍是十七人中最年少者,似我这样才智平庸之人,不知几时才能取得功名。”潇潇笑道:“姜子牙八十出山,佘太君百岁挂帅,公子急什么?”玄纶笑道:“曹娥十四救父,甘罗九岁拜相,你道我如何不急?”潇潇道:“我这是找着茬子安慰你,你倒跟我抬起杠来了。”玄纶笑道:“我也知你是好意,只不过生性如此,不说出来,憋得牙痒痒。”再看这大雁塔高七层,却不似平常的塔为圆形,而是方方正正,棱角分明。近看塔基上,四面都是卿相题咏,更无可题之处了。玄纶上前摸了摸石壁,笑道:“想不到经塔之上,都是官宦文字,又谁知塔内有万卷佛经呢?”
出了慈恩寺,看看到了正午,二人便寻了个酒家用饭。这长安城极是繁华无比,唐时乃天朝国都,东市西市,朝市夜市,共有数万肆坊,每日商贩无数。集市里有个醉仙楼,最负盛名,传说太白曾在此饮酒大醉,写下《将进酒》一诗,故而闻名,玄纶在路上频频听人说起,便有心要去瞧一瞧。玄纶与潇潇一路走来,远远地望见一座酒楼,约有四五层高,飞檐翼角,定是醉仙楼了。二人走过去,酒楼上有“醉仙楼”三个大字,传说是太白醉酒后所题。玄纶向上看去,下面三层人来人往甚是热闹,上面两层倒是清静得很,潇潇道:“看来长安人喜欢热闹,非要大家坐在一起吃酒才能尽兴。”玄纶笑道:“你这机灵鬼,倒是会取笑。”
二人走到门口被小二哥拦住,小二道:“呦,不巧了,今个儿座头都满了,二位客官请去别处吃酒罢。”潇潇道:“你这楼上不是还有两层空着么,怎么就说人满了?”小二道:“上面两层都叫人包了。”玄纶笑道:“是什么人这么有排场,连醉仙楼都包下两层来?”小二道:“是铸币厂的那帮官爷。”玄纶道:“铸币厂的大银监不过五品官秩,他们倒恁地有钱。”小二笑道:“天下的钱都是自他们那里造的,哪儿还怕没钱呢,不够用时多铸些不就好了。”玄纶笑道:“这钱也是混造的。”小二笑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定下了三千多坛上好的女儿红在那里,如何能说没钱?每次来时,还要从得月楼叫些姑娘上来陪酒,搞得这里乌烟瘴气。这帮人一个个脑满肠肥,脾气又坏,伙计们谁都不愿意去伺候。”《醉太平》词云:
纤纤幼伶,牵衣弄形。
小楼歌尽淫声,乐巫山未醒。
哀哀戍兵,操戈奋乘。
大风吹乱长缨,醉他人太平。
掌柜的看到小二跟两个生人说话,恐怕节外生枝,便叫道:“小二,你只管偷懒,还不来招呼客人。”小二道:“二位公子,对面不远处有个小酒家,菜色酒品也不错,二位请便罢。”玄纶拱手道:“多谢小二哥指点。”小二哥唱个喏自去了,二人无奈便向对面走来。走进一会儿,果然有个店面不大的小酒家,向街上挑出一竿酒旗,里面地方不大,人也不甚多。二人找了个桌子坐下,小二见有客人进来,便端了两碗茶过来招呼。小二把茶碗放下,笑着把肩上的手巾拿下了擦了擦桌子,问道:“二位公子可是从醉仙楼过来的?”潇潇道:“你怎知道?”小二摇了摇头笑道:“十个有八个都是打那里来的。”玄纶道:“这是为何?”小二道:“其实那里的酒菜,多数都是前一天晚上打这里送过去的,第二日热一热再上桌,其实就是这里的东西,换了个名目罢了。”玄纶道:“那里没有厨子么?”小二道:“有是有,只是不够使。”玄纶道:“如此,你们倒可以大张旗鼓地抢了他们的生意去。”小二道:“天下人都知道有个醉仙楼,哪里知道有这个地方。我们也乐得有个长年主顾,其实卖给醉仙楼与卖给其他客人也没什么两样。那里有坐不下的客人,也常介绍到这里来,两家也算是互相照顾罢。”正是:
小处卖座头,大处卖名头。
诸君可知,这名头一说,可实实是害苦了小本生意人。就手艺来说,这路边小贩的手艺丝毫不输于那正经酒楼里的厨子,只是苦于无人宣扬,难以发迹罢了。一般的饭菜,这里卖五十文钱,酒楼里就要卖二两银子,手艺又不及这里精细。然而珠无光不明,人无名不富,无奈也只得守着个小摊儿过活,空把这民间上好的手艺失传了,想来真是可惜。如今圣上严旨纠察市井商铺,便总能见一班皂隶在街上横冲直撞,卖弄拳脚,惹是生非,又只敢对支布帐的撒野,不敢对挂牌匾的啰唣,动辄将人打个半死,尽只顾自己显摆威风,却使朝廷背负骂名,真真是岂有此理!如此品质,无论为官为吏,就是拉出去砍个十回八回的也不解气。
话休繁絮,且说潇潇问小二道:“这长安城里有什么特色的酒菜?”小二道:“公子这么问,想必不是本地人了。既然是远方客人,何不品尝一下这里有名的‘……面’?”玄纶没听清楚小二说的是什么什么面,便问道:“小二哥,你方才说的是‘什么什么’面?”潇潇笑道:“我听着像是‘梆梆面’,又像是‘浆浆面’。”小二笑道:“都不是,要说这个字,那可是有学问了,兴许二位公子都不认得。”玄纶笑道:“既然如此,就请小二哥写下来给我瞧瞧。”小二笑道:“小人目不识丁,哪里会写字,不过听说这字非得念着口诀才能写下来哩。”玄纶笑道:“写字还要念口诀,这倒有意思得很,你念来我听听。”小二笑道:“如此,公子听仔细了:‘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东一长西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钩搭挂麻糖,推个小车逛咸阳。’”玄纶用手蘸着茶碗里的水,一边听一边写,写到最后一笔的时候,开始写的那头上一点都已经干了。潇潇道:“叵耐这字,不唱个歌便不肯见人,又见头不见脚,见脚不见头的,像个大姑娘。”
小二笑道:“小的今日可是长见识了,得嘞,我给二位上菜去。”少时,小二端了饭菜上来,玄纶与潇潇吃着,虽然这面有些粘口,然而比江南手擀的细丝面更多了几分嚼头。二人吃完,潇潇唤小二过来会账,只见掌柜的笑着跑过来道:“公子,小人有个不情之请。”玄纶笑道:“掌柜的有甚事但说便是。”掌柜的笑道:“我想请公子给小店题个名字。”玄纶笑道:“小生不善书法,恐怕玷污了贵店的名声。”掌柜的说道:“公子莫要过谦,小店有个名号如何也强于没个名号。”玄纶道:“如此,那小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二连忙过来铺开笔墨,玄纶便提笔写了“生字面坊”四个字。掌柜的赶忙叫小二小心收起来,第二日刻一块匾挂出去,又对玄纶说道:“小人无以为报,这顿饭就算小人做东了罢。”玄纶笑道:“题字乃举手之劳而已,如何能抵当饭钱。”掌柜的再三不肯要,玄纶也只得罢了。从这以后,长安城里便多了一家有名的面坊,游人看这牌匾新奇,纷至沓来,面坊的生意也逐渐兴隆起来,正是:
无论谁家手艺好,声名在外有人来。
下午玄纶要去骊山游玩,诸君听说,这骊山是长安极有名的一座山,东西绵延二十余里,形如骏马,故名骊山。自秦汉以来,代代帝王都于此建有离宫别院,舞榭楼台,至今山间犹有断壁残垣。二人一路走到骊山以北的白鹿原上,此时已近黄昏时分,远远望见灞水上一座长桥,就是灞桥了。两岸杨柳连绵数十里,虽时在深秋,犹能想见暮春景致。古来长安送行者都至灞桥而别,并攀折柳条,吟诗相赠。此时夕阳晚照之中,灞桥身如蘸金,气度恢弘无匹,灞水汤汤而去,似见渺渺征帆。宦游者与妓相别于此,多聚人间离愁。《惜分飞》词云:
自古离愁归灞柳,风雪纷飞时候。
咬破樱桃口,无言相对胭脂扣。
未必罗衾鸳帐久,便把姻缘看透。
请煮青梅酒,寄君千里相思豆。
玄纶与潇潇从桥上走来,如行薄雾之中,彼岸油然若将可越而遥不可及也。行桥上,潇潇指着远处道:“公子,你看。”玄纶望过去,只见骊山之上漫山浸透,层林尽染,流光溢彩,披霞流丹,就如漫山遍野烽火照耀一般。原来骊山上历来满栽枫树,到深秋初冬之时,夕阳西下之际煞是好看,故此将“骊山晚照”列为关中八景之一,实是名不虚传。然而这“骊山晚照”也不是等闲能见的,运气好时才能碰着,故而本地人有“烽火戏游人”之说。说到“烽火”,诸君自然想到“褒姒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今日凭高远眺,犹能见骊山之巅有周幽王与褒姒的望烽台一座,于晚风中绝然而立,梁椽难辨,徒引人吊古之思。《南乡子》词云:
烽火上碉楼,疑是西戎到灞丘。
浩荡三军皆铁甲,诸侯,
褒姒轻舒一靥愁。
草木尽悠悠,汉瓦秦砖土一抔。
宋祖唐宗明古鉴,周幽,
倾国高台万古留。
潇潇问道:“秦始皇的骊山墓,应该就在此处,怎么没一点踪影?”玄纶道:“我看这骊山之下,必有机关。传说有土人在此耕田时掘得陶俑武士头,详之应是墓中之物。《史记》里说始皇陵‘宫观百官,奇器异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若是建于地上,怕不早被人毁坏了。”潇潇道:“坊间应有传言才是。”玄纶道:“嬴政生性暴虐,早知后世会有人盗墓鞭尸,故将造陵工匠一齐杀害埋于陵墓中,故此无人知其确址所在。不过我曾见一本野史里说道‘昔年关中地震,骊山裂地二丈余,现秦陵地宫,铜台玉殿林立,车马珍宝充盈,陶俑武夫不可胜计。有欲穷之者,地阖乃止。’不过所说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潇潇道:“此人穷奢极欲,草菅人命,怪道二世而亡,莫不是遭了天谴?”玄纶道:“报在自身,报在子孙,冥冥中自然早有安排。”《忆秦娥》词云:
烟尘肃,秦居二世阿房覆。
阿房覆,群雄就戮,项刘争逐。
骊山晚照华清沐,凤台依旧歌荣辱。
歌荣辱,时时又续,后庭遗曲。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山顶黑云卷动,一片大好的夕阳景色,从白鹿原逐渐向骊山顶上黯淡下去,最后连望烽台也看不见了。潇潇道,看这样子要下大雨了,这句话还没说完,豆大的雨滴便劈头盖脸地泼下来,打在脸上崩得生疼。玄纶道:“那边有棵大树,我们下去躲躲雨罢。”此时哪里还管得许多,二人拿起脚就跑了过去。喜的是这树枝桠茂密,悲的是这雨倾泻不住,玄纶伸手一摸,雨力甚急,直要把这山河冲个稀里哗啦才罢,却一闪念想起一句诗来,写的恰一似眼前之物,正是: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潇潇问道:“难道此处便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处?”玄纶道:“这算是你问着了,果然就是这里。”潇潇俯身捡起一块石头来,笑道:“说不定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玄纶道:“这不过是传说罢了,何必当真。”潇潇笑道:“我听说书的讲《红楼梦》,宝玉是多出来的一块,既然多了,为何女娲还要舍生取义呢?”玄纶笑道:“那是因为材不堪用才剩下来的,小说里的话自然更不足取信了。”潇潇笑道:“我要是块破石头,自然也愿意到温柔乡里走一遭的。”玄纶笑道:“可是温柔乡里的人,却偏愿意到这大荒山上来走一遭,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过了一晌,雨过天晴,骊山之上夕阳返照,云蒸霞蔚,甚是壮观,玄纶道:“不知褒姒见此情景,肯倾一笑否?”潇潇道:“公子莫要再感慨了,时候不早,该回去了。”玄纶点点头,二人便向回走,随便在街上吃了饭,就回分号里来。玄纶回来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找泰安问话。来福说此时泰安正在账房里,玄纶便匆匆跑到账房里,泰安正满头大汗地拨算盘珠哩。玄纶问道:“伯伯这是干什么?”泰安道:“公子不知,茂财下午不辞而别,丢下这一堆烂摊子。”玄纶讶然道:“如此看来,这厮定是携款潜逃了。”泰安道:“小人细细比对账目,却没有发现大宗出入。”玄纶道:“我早上才算过的,亏空了五千两银子,你把账本拿来我看。”泰安递上账本,玄纶翻阅了一遍,别的还不打紧,看到“玄纶支出白银五千两”一条,不觉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叫道:“这个恶贼,竟然用这样卑鄙伎俩,我去报官拿他。”泰安道:“公子所指何事?”玄纶道:“我只写了‘五十两’,他竟然加了一撇,改作‘五千两’,真真是气煞我也!”泰安道:“这也是公子没有留意,要谢做大写的‘拾’,也不会出这样乱子。”玄纶道:“难不成就这样便宜了他,坏财是小,欺人是大,我这就去衙门。”泰安拉住玄纶道:“公子,这早晚衙门都已歇了,况且目今又没有拿着赃物,如何去得?”玄纶道:“如此,我明日再去。”泰安见玄纶不肯罢手,当夜便跑去茂财家里,只教他死扛不认便了。
第二日,玄纶吩咐潇潇看家,清早便与泰安到衙门前击鼓,知府传上堂来。玄纶先将事情说了个明白,知府乃是有名的断案高手,因见玄纶神色坦然,又见泰安处处小心,便觉得泰安心里有鬼。知府道:“你二人先随我到后堂来,本府有话要私下里问讯。”当即传令退堂,二人随入后堂。知府道:“本府新作一歌,久闻掌柜笔法颇佳,不知肯赐一墨宝否?”泰安忙跪下说道:“既蒙老爷错爱,小人无不从命。”玄纶见知府对泰安亲善有加,却把自己晾在一旁,心里好不是滋味儿,因说道:“以字断案,古今闻所未闻。小生不揣冒昧,亦愿为大人代笔。试看今日之场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老爷笑道:“果然是个年轻气盛的少年。”因教师爷备了两副笔墨来,随即歌道:“唯思事不古,今我已言非。庭中更且草青青,速來歸!”歌罢,二人亦写罢。老爷看了二人笔墨,见泰安字迹虽苍劲稳健,但失于风度,而玄纶笔走龙蛇,神采飘逸,更是赞赏。当下知府并不多说,只吩咐二人后堂等候,自拿了两幅字去了。
老爷到得堂上,立刻掣了一支令签,着当班衙役立时拘捕茂财到案。少时茂财带到,战战兢兢跪在堂下向上叩头道:“小人茂财,叩见知府大人。”知府见他神色慌张,因一拍惊堂木喝道:“有人告你篡改店中账本,可有此事?”茂财道:“小民一向诚实,怎会做出此等事来?”知府道:“如今泰安已然招供下狱,你还有何话说?”茂财道:“小人不信。”知府道:“你若不信,且看他的亲笔字纸。”说着,便教师爷递过一张纸来,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唯慮事不周,今我已認罪。庭中更具草情,請速來歸。”原来知府素有文名,更觉此事颇为有趣,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在泰安所录之歌上略略添上两笔,便成了一纸供状。茂财认得泰安字迹,今见泰安已然把事情交待得明白,自己更犯不着为他顶缸代罪。便把伙同泰安篡改账本,弥补亏空一项说了出来,知府着师爷一一做了笔录,签供画押。再着衙役把泰安押上堂来,将茂财的供词丢给他看过。泰安见茂财已经招了,也只好供认不讳。正是: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今日夕阳已斜,话说至此散场。毕竟泰安与茂财下场如何,且听小子明日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