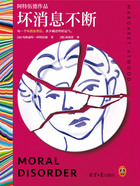
1 坏消息 The Bad News

早晨。夜暂告结束。坏消息该来了。我把坏消息想象成一只巨大的鸟,有着乌鸦的翅膀和我四年级老师的面孔,稀疏的发髻,腐臭的牙齿,布满皱纹的眉头,噘起的嘴唇,等等。在黑暗的掩护下,这只大鸟在全世界游荡,乐此不疲地担当起坏消息的传递者,带着一篮子臭鸟蛋,并且很清楚——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该把它们精准地丢向哪里。比如,丢在我的身上。
在我们家,坏消息伴随着刊登了坏消息的报纸现身。蒂格把它们拿上楼。蒂格的真名是吉尔伯特。和不说英语的人解释这些昵称的由来是不可能的,我也没必要非得这么做。
“他们刚刚杀死了临时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蒂格宣布。这并不是说他对坏消息无动于衷——恰恰相反。蒂格瘦骨嶙峋,他的脂肪含量比我的少,所以,对于坏消息产生的卡路里——坏消息里面确实有卡路里,会让你血压升高——他吸收、消解,并将其转化为身体一部分的能力也比较低。我能做到,他不能。他想尽快把坏消息传递下去——像甩掉一个烫手山芋那样。坏消息会把他烫伤。
我还在床上。我还没完全醒。我还有点沉浸在赖床的感觉里。到目前为止,我还在享受这个早晨。“早餐之前先别说这些。”我说。我没补上的后半句是:“你知道的,这么早,我应付不了这些消息。”我以前说出来过,但收效甚微。在一起这么久,我们两人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与另一半有关的细微告诫和有益提醒——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偏好和禁忌。我看书的时候不要从背后靠近我;不要使用我的菜刀;不要随便乱扔东西。我们都认为对方应该尊重这套经常被重申的指示,但它们是相互抵消的:如果蒂格必须尊重我在早上第一杯咖啡之前随意赖床并杜绝坏消息的需求,难道我就不该尊重他为了让自己尽快摆脱灾难而想把祸事一吐为快的需求吗?
“哦,抱歉。”他说。他责备地瞥了我一眼。我为什么非要这样让他失望呢?我还不清楚吗?如果他不能立刻跟我说出这些坏消息,那么他体内那些让人恶心的绿色的坏消息腺体或者膀胱就会爆炸,他就会患上急性灵魂腹膜炎。到那时就该我后悔了。
他是对的,我会后悔的。除了他之外,我读不懂其他任何人的想法。
“我现在就起床,”我说,希望我的话听起来能让人宽慰,“我马上就下来。”
“现在”和“马上”已经不能代表它们曾经所代表的意义。做每一件事要花的时间都比过去更长。但我仍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日常程序,脱掉睡衣,换上日间装,保养鞋子,滋润面部,挑选维生素片。领导人,我想。临时管理委员会。被他们杀死了。一年之后我不会记得是哪个领导人,哪个临时管理委员会,哪个他们。但是这种报道会成倍增加。一切都是临时的,再没有人能够管理,而且会有很多人,很多他们。他们总是想要杀死领导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么做是出于最美好的愿望。领导人们同样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领导人们站在聚光灯下,杀手们从黑暗处瞄准,很容易命中。
至于其他领导人,他们所谓的先进国家的领导人,那些人其实已经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胡乱张牙舞爪。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出来,那些眼睛四边泛白,像是惊恐万状的牲口的眼睛。如果无人追随,你就无法领导。人们振臂一挥,然后无所作为。他们只想继续过他们的日子。领导人们一直在说:“我们需要更强大的领导力。”然后他们溜掉,去偷瞄他们的民意支持率。都是因为坏消息,坏消息太多了:他们无法承受。
不过,以前也有过坏消息,但我们熬过来了。一提到他们出生之前,或者他们还在嘬手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这么说。我喜欢这种表达:我们熬过来了。意思是那些你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都不值一提,就好像你要加入某个我们的俱乐部,戴上某个写着我们的廉价塑料徽章才够资格。不过,我们熬过来了——这句话仍然令人振奋。它变幻出一场行军或者列队,马蹄腾跃,戎装由于围困或者战斗或者敌军占领或者勇屠恶龙或者在荒野中跋涉了四十年而破烂不堪,布满泥泞。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领导人高举他的旗帜,指向前方。领导人会提前知道坏消息。他会知道,他会理解,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从侧翼进攻!直击要害!滚出埃及!诸如此类。
“你在哪儿?”蒂格朝着楼上喊道,“咖啡好了。”
“我在这儿。”我朝楼下回应。我们经常这样,把空气当成对讲机用。我们没有丧失沟通的能力——尚未。尚未是个引而不发的词,就像是Honour里不发音的字母h。尚未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会把它说出口。
这些就是此刻定义我们的时态:过去时,曾经;将来时,尚未。我们生活在两者之间的狭小空隙中,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为这个空隙应该叫作仍然,而且实际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的空隙更小。确实,我们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一会儿是膝盖,一会儿是眼睛——但到目前为止都只是小问题。只要我们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就仍然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我还记得,我们的女儿还是青春少女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逗过她。我假装自己已经变老了。我走路撞墙,手里握不住刀叉,假装失去了记忆。然后我们都笑了。但这不再是个玩笑了。
我们已经过世的猫咪鼓丘[1],在17岁的时候患上了猫科动物衰老症。鼓丘——我们怎么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另外一只猫,先走的那只,叫冰碛。我们以前觉得,用冰川堆积而成的地质特征来命名我们的猫咪是很有趣的事情,但这么做的意义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蒂格说,鼓丘应该被叫作“垃圾填埋场”,但是给它清理猫砂盆是他的活。
我们应该不会再养猫了。我曾经想过——相当冷静地思考过——蒂格走后(因为男人会先死,不是吗?),我可能会再养只猫做伴儿。我现在已经不考虑这个选项了。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已经半瞎,那只猫会在我的腿脚之间跑来跑去,我会被它绊倒,摔断脖子。
可怜的鼓丘一到夜里就在房子里潜行,发出神秘莫测的诡异号叫。什么都不能给它慰藉:它在寻找它丢失的东西,可它不知道那是什么。(实事求是地说,是它的理智,如果猫也有理智的话。)很多个早晨,我们会发现番茄或者梨子上有小口啃噬的痕迹:它忘了它是肉食动物,它忘了它应该吃什么东西。这已经成为我对未来的自己设想的图景:在黑暗的房子里徘徊,穿着白色睡衣,为我不太记得的失去的东西而号叫。那让人难以承受。我在半夜醒来,伸出手去确认蒂格仍然在身边,仍然有呼吸。目前为止,还好。
我走进厨房时,里面弥漫着吐司和咖啡的香气:我并不意外,因为那就是蒂格准备的早餐。那气味像毛毯一样包裹着我,当我真正吃到吐司、喝到咖啡的时候仍徘徊不去。桌面上,是坏消息。
“冰箱一直在响。”我说。我们不太注意维护家电。我们俩都是。冰箱上贴着一张我们女儿的照片,几年前拍的;她笑吟吟地看着我们,仿佛一颗远去的恒星发出的光。她正忙于她自己的生活,在其他地方。
“看看报纸。”蒂格说。
报纸上有照片。配上照片的坏消息会更糟糕吗?我认为是的。无论你愿不愿意,照片都会吸引你的目光。照片上是一辆被烧毁的汽车,是迄今为止被烧掉的很多车里的一辆,烧得只剩下扭曲的金属框架。一个焦黑的影子蜷缩在车里。这种照片中总是会有空荡荡的鞋。正是那些鞋让我心烦意乱。正是这件每天都要做的最平常的事情——抱着去往某个地方的坚定信念而把鞋穿在脚上——让人悲伤。
我们不喜欢坏消息,但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动向,以防它冲着我们过来。草地上有一群鹿,正安静地低头吃草。然后汪汪——树林里有野狗。群鹿抬起头,耳朵转向前方,准备逃跑!或者释放麝香进行防御:因为最新消息是狼来了。快——围成一圈!雌鹿和小鹿在中间!喷鼻刨地!准备用鹿角顶向敌人!
“他们不会停手的。”蒂格说。
“太混乱了,”我说,“我想知道当时安保人员在哪儿?”他们那时常说,上帝分发大脑的时候,一些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人排在了最后。
“如果有人真想杀你,他们就肯定能杀了你。”蒂格说。他是那种宿命论者。我不同意,于是我们花了一刻钟的时间愉快地传唤了已经死去的证人们。他提出了斐迪南大公[2]和约翰·肯尼迪;我提出了维多利亚女王(八次失败的刺杀行动)以及用大量暗杀来避免自己被暗杀的约瑟夫·斯大林。以前,这会成为一场辩论。现在则只是消遣罢了,就像金拉米纸牌游戏一样。
“我们是幸运的。”蒂格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仍然都坐在厨房里。没有人离去。尚未。
“是的,”我说,“看着点吐司——要烧焦了。”
好了。我们已经处理了坏消息,我们直接面对了它,而且我们没事。我们没有受伤,没有血从我们身上涌出来,我们没有被烧焦。我们的鞋也都还在。阳光明媚,鸟儿啾鸣,没有理由不让人觉得美好。大多数时候,坏消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爆炸、原油泄漏、种族灭绝、饥荒,所有一切。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消息。总会有的。等它们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担心吧。
几年前——什么时候来着?——蒂格和我在法国南部一个叫作格拉诺姆的地方。我们算是去度假的。我们真正想去看的是凡·高画出鸢尾花的那座疯人院,我们也如愿看到了。格拉诺姆是附加行程。我好多年没有想起过那次旅行了,但我发现自己此时就在那里,在曾经的格拉诺姆,在它于三世纪被毁灭之前,在它只剩下几处你付钱才能进入的废墟之前。
格拉诺姆有许多宽敞的别墅,还有公共浴室、露天剧场、神庙等那类罗马人走到哪里都要兴建起来,好让自己感受到文明与自在的建筑。格拉诺姆非常怡人,军方很多高级将领退休后都住在这里。这里的文化相当多元,相当迥异:我们也喜欢新鲜事物和异国情调,但没有罗马人那么喜欢。我们这儿还是有点守旧。不过,我们仍然有来自各地的神,当然,是在官方的诸神之外。比如,我们有一座供奉西布莉[3]的小神庙,上面装饰着两只耳朵,象征着你愿意为她献祭的一部分身体。人们对此开玩笑:他们说,只砍掉耳朵就能过关,算你们走运。丢掉耳朵总比丢掉性命强多了。
在罗马式家庭中还夹杂着一些更为古老的希腊式家庭,一些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也仍然在留存延续。凯尔特人进城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与我们一样的宽袍和斗篷,说着流利的拉丁语。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已经足够友好,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猎首[4]的方式。蒂格不得不安排一定程度的招待活动,我也曾经邀请过一位重要的凯尔特人来用晚餐。这么做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但问题不大:我们的客人表现得相当正常,醉意也刚好保持在不会失礼的程度。他的头发很奇怪——微红并卷曲着——他还戴着很有仪式感的青铜项圈,不过他并不比我能想到的其他一些人更凶残,虽然他的礼貌确实有些瘆人。
我正在装潢着波摩娜与西风女神[5]壁画的客厅里吃早餐。画家的水平并非一流——波摩娜有点斜眼,而且胸部巨大,可是在这里你并不一定找得到一流的画家。我在吃什么呢?面包、蜂蜜、无花果干。这时还吃不到时令水果。没有咖啡,真倒霉;我认为当时咖啡还没问世。我在喝一些发酵的马奶,帮助消化。早餐是一个忠实的奴隶用银托盘端来的。他们是这个家庭里很好的奴隶,他们很在行:他们寡言、谨慎、高效。他们不想被卖掉——那是自然:做家奴总好过在采石场做苦役。
蒂格拿着一个卷轴进来了。蒂格是他以前在军队里的外号“底格里斯”的简称。只有几个铁哥们才会叫他蒂格。他皱着眉头。
“坏消息?”我问。
“野蛮人入侵了,”他说,“他们已经跨过了莱茵河。”
“吃完早餐再说。”我说。他知道我起床后不能马上谈论沉重的话题。但我的语气太生硬了,看到他哀伤的表情,我心软了:“他们总是在跨过莱茵河。让你觉得他们自己都烦了。我们的军团会击败他们的。以前一直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蒂格说,“我们就不该让那么多的野蛮人参军。他们靠不住。”一方面,他自己在军队里待过很长时间,所以他的担忧能说明一定问题。另一方面,他的总体看法是罗马正在加速走向灭亡,而且我注意到,大多数退了休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这个世界缺了他们就完全无法运转。他们不是觉得无能为力,他们是觉得无用武之地。
“好了,坐下,”我说,“我来帮你点一大份面包和蜂蜜,配上无花果。”蒂格坐下了。我没给他点马奶,虽然那对他有好处。他知道我知道他不喜欢那玩意儿。他讨厌别人念叨他的健康,最近他的身体出了一些小状况。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吧,我默默地向他祈祷。
“你听说了吗?”我说,“他们发现了一颗刚刚被砍下来的人头,就挂在那口凯尔特祭祀古井的旁边。”好像是个从采石场逃出来跑进森林的工人,他们之前就警告过他,天晓得。“你觉得他们会重新信仰异教吗?那些凯尔特人?”
“他们恨我们,真的,”蒂格说,“纪念拱门也没任何帮助。这根本不是策略——凯尔特人被打败了,罗马人把脚踩在他们头上。你没注意到他们一直盯着我们的脖子吗?他们很愿意插一把刀子进去。但他们现在软弱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奢侈。不像北方的野蛮人。凯尔特人知道,如果我们完蛋,他们也会完蛋。”
那块好吃的面包他只咬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四处踱步。他看上去满面通红。“我要去趟浴池,”他说,“去打听消息。”
去听听传闻和流言,我想。先兆,预感;飞鸟,羊肠。你永远不会知道消息的真假,直到它发生的那一刻;直到它突然落在你的头上;直到你在夜里伸出手,却不再有呼吸;直到你在黑暗中号叫,穿着你的白色睡衣,在那些空荡荡的房间里徘徊。
“我们会熬过去的。”我说。蒂格什么都没说。
那天的天气是那么好。空气中有百里香的味道,果树上繁花盛开。但是这对野蛮人来说毫无意义;实际上,他们更愿意趁着好天气入侵。他们的劫掠和屠杀会有更好的能见度。我听说,就是这群野蛮人把受害者塞满柳条编的笼子,点燃,作为供奉他们神灵的祭品。不过,他们仍然很遥远。就算他们成功地跨过了莱茵河,就算他们没有成千上万地被杀,就算他们的鲜血没有把河流染成红色,他们也要很久之后才会到达这里;或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都不会。格拉诺姆没有危险,尚未。
[1] 亦称蛋丘,冰川堆积作用形成的一种小丘,形如半卵覆置。——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或译者注)
[2] 奥匈帝国皇储,1914年视察奥匈帝国波黑省的首府萨拉热窝时遇刺身亡,此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3] 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
[4] 凯尔特人最初出于宗教目的进行猎首活动,以此来为部族增加精神力量;之后主要用这一行为来提升自己的威望。中世纪时期,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之后,这一行为逐渐减少。
[5] 分别为罗马神话中的果树之神和希腊神话中用西风带来春天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