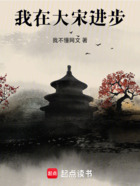
第2章 措不及防的拜师
时间过去许久。
姜塬把煎好的药汤倒出来,唤一声傅指挥使来端走,对于床榻上白发老者的身份,他内心颇为好奇,问道
“傅大哥,那人是谁呀?你好歹也是徐州城里领兵五百士卒的指挥使,地位也非平头老百姓了,值得一大早寸步不离的跟着。”
这姜小子属狗的变脸真快,刚才还骂他歹毒,现在叫起大哥了。
傅指挥使端着药汤,悄咪咪的嘀咕一句“范公范仲淹,你小子走运了。”
救命恩情的重量已经不言而喻,纵使庆历新政之后,范仲淹没回中枢任职过了,但是他宦海沉浮一生,所积攒的名望、人脉依旧非常的重。
大宋官场敲门砖。
范仲淹?
岳阳楼记…
姜塬身体突然的僵住,他把名垂青史的范仲淹救活了,历史他只略知一点点,脑子里记得范仲淹会在皇祐四年死去,却没太注意在什么时间、地点。
傅指挥使看见姜塬吃瘪,心满意足的把药汤端走。
姜塬缓缓坐下,心中盘算着他若是拜范仲淹为师,岂不是能大大增加中举的机会?
作弊是不可能作弊,但是范仲淹考中过进士,具备一定的考试经验,学识又渊博,若受他指点一二,肯定比别人领先一大截不为过啊。
况且救命之恩在手,大不了用道德要挟一下,死也要拜入范门。
大宋官场纯粹就是人脉场,没高官保举你,想晋升就慢慢熬资历,一熬一个不吱声。
姜塬打定主意,心情愉快的把陶罐子里的铜针倒出,然后再扔进以黄柏、艾草、金银花等药材熬出的药汁泡着,进行双重消毒。
铜针消毒的效果绝对比不上后世,却也是当下最好的了。
炭火和药材均是要钱。
随后不久,徐州的知州和通判等数名本地官员亲临姜氏医馆看望床榻上的范仲淹,临走之前又免除姜塬个人三年的赋税徭役。
……
六月二十一日。
“徐州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几十余次,是非曲直、难以论说……”
医馆里,响起姜塬抑扬顿挫的声音。
而在他眼前的孩童,则是听得一愣一愣的,完全没看到一枚锋针已经临近。
受工艺限制,古时的铜针说细不够细,说粗也不太粗。
至少视觉上令人挺害怕的,孩童自是不必多言了。
姜塬想着法子哄幼童,在他注意力分散时刻,以摩擦出火星子的手速,点刺四缝穴,挤出少量的粘稠血液,其中还混合着黄白颜色。
小儿疳积症,面色萎黄,精神萎靡,夜间低热,舌淡苔白腻,指纹淡紫滞,腹部膨隆,体型消瘦。
五周岁的孩童错愕一下,感觉到疼感后,立马放声哇哇大哭。
陪在孩童身边,一名妇人打扮的娘子,立刻抱起来哄着。
“娘饿,娘饿…”
“快去给他喂些食物,五天后再来一次,便可痊愈了。”
姜塬清洗双手的同时,嘴上没停下来。
“谢谢姜大夫。”那娘子留下足够的铜钱转身而去。
“姜神医,我家大相公想见你,可否有空?”
此人从后堂里走出,言语相当的客气,是服侍范仲淹的另外之人。
经过两日的休养范仲淹病情已经有所好转,说话有劲,独立吃食不是问题。
姜塬算着也该把拜师之事落实了,不然心中没个底。
后堂里有五间屋子,原身的爹和他各一间,灶房、药材房、茅房又各占一间。
现今范仲淹住在姜塬他爹的屋子养病,碍于人已六旬,人老体弱,刚大病一场,本地官员没敢移去官驿,生怕路上出现点意外了。
屋子里生有火盆,燃烧着一颗颗的枣木炭,烟尘稀少,火力旺盛,乃上等木炭,多流通于权贵阶层。
枣木炭雕刻成兽形,则是兽炭。
时值六月天,屋中的圆脑袋男子在封闭炎热的空间和高温天气烤炙下,额头、后背已经挥汗如雨,浸湿了衣衫,却没提出离开意思。
床榻上的范仲淹,半起身子,靠在枕头绵柔之物,下半身盖着蚕丝被子,神色平静,全无半点汗意。
“等会人来,你出去歇息一会儿吧。”
“是,范相公。”
少顷。
屋门裂出一道不大的缝隙,姜塬的身子,宛如泥鳅一样滑溜的钻进来,那啥润滑之物,都没他身形有效果。
然后姜塬察觉圆脑袋男子对他发出救星般的目光,后脚跑了出去。
好热…
姜塬瞬间体会到圆脑袋男子的举动了。
范仲淹早年久任西北,新政失败后,又被调去西北,身上的疾病多是天寒地冻造成,外加人老体能衰弱,公务繁身,体内的阳气属于严重不足,所以当下的火盆对范仲淹不算什么,对其他人才是一大弊端。
“小友的救命之恩,老夫心中不胜感激,老命一条,没想到还能苟延残喘于世。”
“范相公言重,大宋还需要您这样的官员去治理,官家也亟需您的才能去教化老百姓。”
姜塬一脸的严肃,全程没有半点笑意。
然后,未等范仲淹继续出言。
他就噗通一声,直接跪下去,王炸明牌。
“小子姜塬,从小仰望范公之名,苦读诗书多年就是希望成为您一样的人,今日有幸面见范公,恳请收我为学生,教导为人处世之理。”
这…这…这……
范仲淹正想抒发心中的感慨,完全没预料到会被人来这招,换作其他人,他自然有底气严词拒绝,姜塬则不行。
“你家中还有长辈吗?”
“家母难产而死,家父为穷苦百姓四处行医,已于三年前劳累过度身亡,因家父祖籍地早年遭受天灾,为了生活迁至徐州,族亲四散各地,没法联系得上了。”
姜塬两指大力一拧大腿,痛的眼泪直流。
这样的遭遇,好像也没法拒绝。
范仲淹有着丰富的主政经验,没有一口应承下来,继续询问:“你读过几年的书?学识不深的话,老夫修书一封引荐你去应天学府,所需的费用也可全免了。”
“本朝受太祖太宗的影响,自上而下,文风昌盛,家父自是不可避免,自小就送我去官学,夫子布置的学业更是不敢有所怠慢,错一道便是一棍子伺候,至今已读书七年,熟背九经典籍。”
这话可不是姜塬吹牛,原身的父亲就是用棍子抽着原身读书,希望他有朝一日高中进士。
国策如此,也能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