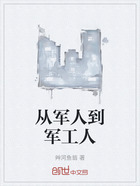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7章 背起书包进学堂
1966年9月,七岁的我背上书包跨进了学堂,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我就读的CQ市JLP区第十六小学,创建于1957年,原名“CQ市JLP区杨家坪第二小学”(简称“杨二小”),1978年更名为“CQ市JLP区谢家湾小学”,1981年评为SC省首批重点小学,1999年评为CQ市首批示范小学。
JLP区十六小学位于重庆城西两杨(两路口至扬家坪)公路谢家湾车站旁的一个小山坡上。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走上去,沿途有几个零星的农村院落,房子四周丛篁修竹。遍坡的农田菜地,有的种着当季农作物;有的种着时令蔬菜。
学校位于坡顶的台地,几幢建筑物围着铺煤渣的四方型操场修建。操场的正前方有一个高约一米左右的宽敞舞台,舞台后面是一幢四层楼的教学大楼;操场的后面是一幢作为学校办公室和老师宿舍的两层小楼;操场的左面,有一溜兼作教师食堂和库房等的平房;操场的右面,是一个高出操场一截的土坎,栽植着整齐的树木。
走出学校站在土坎上,可以远眺闻名遐迩的长江九龙滩,近看两扬公路穿越谢家湾的建设厂工业区。军工厂成片的高大厂房从生长着郁郁葱葱黄葛树的鹅公岩,一直绵延到长江岸边。鹅公岩下面是成渝铁路上的三孔桥,三孔桥外面的长江河道,在九龙滩绕了一个大弯,形成了流经重庆城区的最宽江面。弯道的入口是九龙坡码头,弯道的中间是建设厂码头,弯道的出口是黄家码头。
顺着两扬公路往上看,可以看见袁家岗的重庆医学院和西南物管处,以及袁茄(袁家岗至茄子溪)公路路口处的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往左看隐约可见远处的高峰,是佛图关和佛图关前面的鹅岭上的红星亭;往右边看,近在咫尺的两杨公路那一端高矮楼房交错的地方,就是热闹繁华的杨家坪。
报名以后,从周一至周六的每个早晨,我都会背上书包,手里拿一个母亲给我蒸热的大馒头(有时是烤红苕或煮苞谷)和茶叶鸡蛋,相约街上的邻居同学,一起走路到学校去上学,风雨无阻。
但我们上学要抄近路,一般都不走谢家湾公路这条路,太绕了。我们从鹤兴路出发,过长江路街口,然后穿过杨家坪大转盘,走到两杨公路拐弯处的扬家坪供电站,离开公路爬上路边的一段缓坡,就进入了建设厂职工家属区的劳动三村,在一栋栋白墙青瓦的平房和工字型两层红砖楼房中穿出村子,途经九龙公社大片菜地的两个小山丘之间的一条小山沟,拐进一百多米长的建设厂清水池院墙与重庆工业管理学校游泳池院墙中间狭窄的小路,还要爬上高低起伏的菜地中大约几百米的一段上坡土路才到学校。
对六七岁的小孩子来说,路有点远。遇到刮风下雨,要拢学校的那段土路相当泥泞,因为路滑而经常摔跟头,求学之路甚为艰难。
那时上学读书的学费很低,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总共只要几元钱。各科的课本由学校统一发放,作业本和铅笔等学习用具则自己买,只要几角钱,很便宜,几乎所有的学龄儿童基本上都上得起学。
我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学校报到时,新同学们大多背的是军用挎包款式的黄绿色帆布书包,个别家庭困难的同学背不起书包,便用人造革简易手提袋当书包。文具中,有塑料或铁皮的文具盒,铅笔是带橡皮头的六棱铅笔,塑料的垫板和尺子,还有上图画课的蜡笔等等。
记得我上小学时被分到一年级2班。走进教室,正前方是一张大黑板,黑板上方中央贴着彩色的毛主席标准像,标准像两边是毛主席手书体条幅,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依稀记得学校对一年级新生开设有语文、算术,还开有体育、音乐、大字、图画等几门课,上二年级以后,又陆续开设了政治、常识、珠算、美术、自习等课。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社会上“读书无用”的观念开始泛滥,学校的教学也受到严重影响。开学时,课本到得不是很齐全,有些课的教材发放不及时。没有课本的课,有时就读报纸。教学秩序也不是很正常,教师们经常要开会学习,上课耽搁很大。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举行学习会,学习会后,有时也布置一些作文。有的同学都随便涂鸦,交差了事,但我却认真对待,写的作文往往脱颖而出。不知怎的,我从小就不善言词,但是一拿起笔来,似乎就有说不完的话,所以我最喜欢上语文课。小小年纪的我写的学习心得体会或者紧跟形势的打油诗,有时还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由于我练习过毛笔字,字写得相对周正一些,有时还被张贴在学校的橱窗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刮目相看。
我们小孩子还不懂学习的重要性,也不懂父母深信不疑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只觉得上学挺好玩,缺乏刻苦攻读的动力。
我的父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却对学校现状忧心仲仲。“学而优则仕”何以能成为中国人长久信奉的文化传统?孟子那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制,为博取功名而刻苦攻读之风便盛行不衰。在那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科举之路成为了唯一能使人人皆有机会平等竞争的晋升之途。历经千年推行的科举制度,致使官本位意识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或许这些观念在当下看来略显陈旧,但其背后,实则是人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一美好善良愿望的自然呈现。直至今日,勤奋读书、考取理想学府,依旧是各阶层人士谋求脱颖而出、出人头地的最佳途径。
家父是豁达的。他常常讲,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虽然对当前现实颇为无奈,但既然是现实,就要客观地面对,不妨以自学为途径,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学习的困境,实现“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景愿。
所以,虽然学校教学相对宽松,父母仍旧对我的学业要求极为严苛。学校上课时没有考试测验,下课后不布置作业,但我并不轻松,因为下课回家后,往往有一大堆父母布置的作业在等着我。
其实早在上学以前,还处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我,就已经开始了识数认字了。
父亲向来持有一观点,即“阅读与书法,可助人修身养性”。大抵从两三岁起,父亲便倾心于对我启蒙,常翻开简易画册,逐字逐画地耐心教我辨认,悄然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
父亲是照相馆修修底片的技师。那时候,顾客常常要求在底片上留下毛笔题字,以作留念或标注。为满足需求,父亲的工作台常年整整齐齐摆放着笔墨纸砚这一套文房四宝,随时备用。
父亲极重子女教育,心思细腻的他灵机一动,将相馆报废的相纸收集起来,剪成巴掌大的小方块,在背面用毛笔工工整整书写汉字,精心制作成一张张识字卡片。每日闲暇之余,便会拉着我,耐心地教我认读简单的汉字。只可惜,武斗中的一场无情大火肆虐而过,父亲辛苦积攒、饱含心血的识字卡片,就此毁于一旦,每每念及,心中满是遗憾。
上小学后,父亲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又开始教我吟诵一些韵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儿歌,还有那一首首韵味无穷的古代诗词。他巧妙地借助诗词,一边教我识字断句,夯实文化基础;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诗词背后的故事,引领我走进文学的奇妙天地,让尚处在懵懂无知启蒙阶段的我,对学习萌生了无尽的热忱与兴致。
回首往昔岁月,父亲曾教过我的诸多儿歌与诗词,在时光的冲刷下,大多已在记忆深处渐渐模糊不清。然而,有一首别具一格的字谜诗,却如同镌刻在心底一般,至今印象深刻。那诗写道:“园中花,化为灰,夕阳一点已西坠,相思泪,心已碎,空听马蹄归,秋日残阳萤火飞。”犹记当年,父亲面带微笑,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是大文豪苏轼所作的一首精妙绝伦的字谜诗,其谜底正是繁体的“蘇”字。这简简单单的一首诗,承载的不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父亲对我深沉的爱与殷切的期望,成为我成长路上熠熠生辉的珍贵记忆。
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在中华浩浩荡荡数千年的文化长河里,苏轼宛如一颗最为耀眼夺目、熠熠生辉的巨星。他行文之时,笔锋恰似灵动游龙,婉转蛇行,落下的每一个汉字,都仿若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绽放着深邃幽远、震撼人心的思想华光,叫人见之不禁拍案叫绝,由衷地叹为观止。苏轼实乃对华夏文化发展进程影响深远的一代巨匠,后世之人无一不将其尊崇为文人墨客的典范楷模。母亲听了父子对话,也特意步入厨房,精心烹制了那两道传颂至今的经典名菜——东坡肘子与东坡肉,还笑意盈盈地对我说道:“苏东坡可不单单是擅长舞文弄墨的大文学家,还是精通饮食门道的美食大家呢,这两道菜便是明证。”
父亲还曾利用给我讲故事的机会,提及苏轼那可是苏姓一族漫漫岁月长河中,极具分量、影响力非凡的伟大人物之首。回首往昔,苏姓先辈里另有诸多豪杰之士。遥想战国之时,那位声名远扬、家喻户晓的纵横大家、外交贤能兼谋略高人苏秦,凭借自身经天纬地、超凡脱俗的才智,周旋于六国朝堂之上,身佩六国相印,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书写了一段段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传奇史诗;再观西汉年间,大臣苏武奉旨出使匈奴,却惨遭无端扣押,被放逐至北海之滨牧羊,一十九载寒来暑往,他始终手持汉家符节,坚贞不屈,那股忠贞不二的凛然正气、炽热赤诚的崇高爱国情怀,穿越千年历史风云,至今依旧为世人所敬仰、所赞叹。
承蒙这些古代先贤如此高风亮节与超凡卓绝人格魅力的滋养熏陶,刚踏入学堂的我,便牢牢记住了苏轼之名。
后来,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本中那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阕时,旁征博引、绘声绘色地系统阐述了历史上苏轼跌宕起伏的生平轶事。其间那句神来之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仿若一道澄澈甘冽的清泉,缓缓流淌、潺潺注入我的心间,自此便如同镌刻印记一般,深深烙印于我脑海深处,让我首度真切领略、体悟到中华文化那含蓄深沉、动人心弦的韵味之美。
此后,随着学业逐步精进,我又接连研习了苏轼大量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鸿篇巨制,还有幸品鉴其精妙无双的书画珍品与笔力万钧的书法真迹。刹那间,我仿若置身于文化的浩瀚宇宙,再度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邃精微所深深震撼,对苏轼豁达洒脱、超凡入圣的人生境界满怀尊崇敬仰之情,于他那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倾心仰慕不已,更为他那如巍峨高山般令人仰望的人格魅力所彻底折服。
于我而言,苏轼对我影响最深、犹如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的,当属那句至理名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自年少青涩之时起,苏轼这位才情纵横、冠绝古今的华夏古代思想家,名垂青史、受万人敬仰的文坛巨擘,便被我视作文化神明尊崇备至,成为虔诚地顶礼膜拜的心中偶像。
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崇仰之情,我在读小学时,内心便萌生出对考入大学深造的深切向往。
在父母的督促下,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拔尖,尤其是语文成绩较为突出,受到学校老师的重视,一年级开学不久便被指定为班长。
1967年6月1日,是我上学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那天学校放假,大人们照例要为生计奔波。早晨,父母给了我几角钱就去上班了,我便与十几个一般大小的街坊小伙伴相约,到大家经常光顾的动物园去游园。
那天是星期四,阳光明媚。我们一大群男娃女娃刚上街,就听到一个挑着担子的嬢嬢“卖麻汤啰!卖麻汤啰”的清亮嗓音。麻汤是一种由麦芽发酵而熬制成的糖,颜色白中带黄,昧道纯甜,粘性极强。嘴馋的我们立即围了上去,嬢嬢的担子里用簸箕盛着板结的两大块麻糖。面上撒一层白色的米粉,撒着星星点点的芝麻,她用钉锤敲着箕子,将麻糖錾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放在秤盘里称出斤两。小伙伴们纷纷掏钱,一人称了一大坨麻汤,悠哉游哉边吃边走。
来到公园的大门口,游园的大人小孩人山人海。售票窗口人太多,买票的轮子太长,乱哄哄的挤成一团,有戴红袖笼的大人在维持秩序。
我们这一群小崽儿中,有几个读小学二三年级的大同学,这种场合自然由他们拿主意。一个读三年级的女同学主动站出来,她把大家的门票钱收起来,安排另一个读二年级的崽儿去排队买票,其余的小崽儿就远离人群,蹲在大门左面的石桥当头等候。
远远看到买票的轮子缓缓移动,三年级娃儿离售票窗口还远得很,短时间排不拢去。究竟耐心等轮子还是另找耍处?便有了分歧。就在大伙举棋不定时,有个一年级的小崽儿嗫嚅着说,他知道在熊猫山那边公园的一处院墙,最近被雨水冲挎了一个豁口,可以翻进去。
听说有机会逃门票,大家跃跃欲试,这样的事我们经常干。几个二三年级的娃儿商量一阵后也变了卦,决定去翻院墙。几个一年级的小娃儿自然言听计从。大哥哥姐姐们把门票钱一一退还,带领大家就绕了一个大圈,走了半个小时左右,到了公园熊猫山外面的山脚处。
走拢才看到,修在半山腰树林中的院墙果然垮了一小块,豁口离地面只有一米左右,院墙内外的杂树林没有路,比较隐蔽。我们悄悄地靠过去,手脚麻利地接二连三攀爬进去。想到节约了门票钱,大伙都很得意。
认知摸索着还没有走出密集丛生的树林,就听到公园里面远远传来一阵骚乱,好多人在大声尖叫,非常刺耳。
我们立即听出情况不大对头。由于翻院墙被追赶是家常便饭,我们还以为是被执勤的大人发现了。大家遭吓坏了,一个个又争先恐后地从豁口翻了出去,跌跌撞撞地跑到山坡下面的马路边的树林里。脸青面黑地躲藏了好一阵,并没有发现有戴红袖章的大人追出来,小家伙们这才缓过神来。
这一折腾,小半个上午过去了,但谁也不敢再翻院墙了。一群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家伙,七嘴八舌的闹腾一阵,终于统一了意见:还是老老实实到公园大门买票进去吧。于是一伙人又慢吞吞地沿着石板路往回走。
回到公园的大门口,就看见轮子已经散了,但乱哄哄的围着许多人,其中还有一些警察,不让闲人靠近。什么情况?我们很纳闷,于是钻进人群里去看个究竟。
我们看到大门外的院墙边摆放有好多个大箩篼,里面装满了小孩遗失的鞋子、衣物、玩具、食物和其它物品。一群小崽儿这一下才搞清楚:是说不得刚才公园里面哦豁翻天的愣大阵仗,原来是出大事了。
我们一边吃麻汤一边躲得远远的看热闹,不料我们街上好多小孩子的家长闻讯后都焦急的找来。鹤兴路离公园很近,我父亲跟几个有小孩来逛公园的同事一起,气喘吁吁也来了。他一走拢就把我一把揪住,不由分说拖起就走,害得我还没有吃完的一半麻汤掉在地上都不准我捡。
我使劲挣扎想捡回来,结果脑壳上立即挨了两磕钻(指来自长辈对晚辈的责备方式,用食指和中指并拢,然后弯曲,用最突出的那部分关节去敲打小孩的脑袋),痛了好几天。
后来我才听人讲,那天上午动物园里游客太多了,有人可能出于恶作剧,讹传“老虎出来了”,没想到弄假成真,引起了众人恐慌,整个公园顿时乱了套。大人小孩拥挤着拚命往公园大门跑,形势在瞬间失去控制,结果混乱中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悲剧。
那天提出“翻院墙”的崽儿,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字了,不过全靠他想精想怪,才让我们这群小崽儿阴错阳差地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