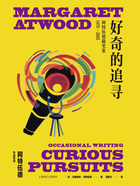
夏娃的诅咒——或者说,我在学校所学到的
曾经一度,我今天是不会被请来给你们演讲的。那并不是在很久以前。一九六〇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大学学院的英语系是不会聘用女性的,无论她们资质如何。我上的学院倒是聘用女性,只是不会让她们很快地升职。我的一位老师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研究领域受人尊敬的权威。她在成为柯勒律治领域受人尊敬的权威很多年后,才有人发觉有必要把她从讲师的岗位上提拔上来。
幸运的是,我本人并不希望成为柯勒律治方面的权威。我想当作家,但作家,就我所见到的而言,赚的还不如讲师多,于是我决定去念研究生。即便我真的有过要在学术上有所造诣的雄心抱负,在一位教授问我是不是真的想去念研究生……难道不会更情愿嫁人的时候,也都转而变成怨恨了。我认识几个完全可以选择用婚姻取代事业的男人,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出于客观机缘,或者也是出于主观意愿,一直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出了名的有始无终。
“等我三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就必须在婚姻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这话什么意思?”我问他。
“这个嘛,如果要结婚,我就必须有事业。”他回答。
而我却被要求二者选一。许多事情随时代而改变,我希望这也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没有哪个思路正常的大学会举办名叫“女性谈女性”的系列讲座。就算真的要就这一主题讲些什么,多半也会请来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一个男性,来探讨女性天生的受虐倾向。为女性提供大学教育,哪怕被认为是正当的,也是基于这能让女性成为更有聪明才智的妻子和更见多识广的母亲。女性问题方面的权威往往都是男性。他们被认定掌握着这方面的知识,就像掌握着其他所有的知识一样,而理由仅仅只是他们的性别。如今局面扭转,女性被认为理当掌握这些知识,仅仅是因为她们身为女性。我只能认为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被请来给你们演讲的,因为我在女性问题,确切地说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不是什么权威。
我逃离了学术,也绕开了记者行业——这也是我曾经考虑过的职业,但有人告诉我女记者最后通常都会去写讣告,或者是给女性版面写婚礼公告,很符合她们的古老角色,掌控生死的女神、婚床装饰者和遗体清洗人。最终我成了一名职业作家。我刚刚完成了一本小说,所以我想以一个现役小说家的身份来探讨这个广泛的话题。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是每个小说家,无论男女,在从事写作的某个阶段都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个文学评论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小说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该履行什么功能?应该给读者带来什么好处,如果真能带来好处的话?它究竟应该取悦还是施教,还是两者兼有,而如果是两者兼有,让人感到愉悦和让人获得启发之间是否会有矛盾?小说应当探讨假想的可能、真相的陈述,抑或只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究竟是要关注一个人应当怎样度过人生,怎样才能度过人生(通常更加局限),还是大多数人如何度过人生?它是否应该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社会的一些事实?它能对此避而不谈吗?更具体地说,假如我在写一本由一位女性担任主角的小说;我应该在上述问题上安排多少篇幅?由于批评家先入为主的成见,我又不得不在上述问题上安排多少篇幅?我是否想让主角讨人喜欢,受人尊重,或是获得信任?她能同时满足这三点吗?喜欢她、尊重她,或者相信她的人各自都会带着哪些假设?她一定必须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吗?
我不喜欢“榜样”这个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情形。那是,当然是,在大学里,一所整体上由男性主导却有一间女子学院附属其中的大学。女子学院正在物色一位院长。我的朋友,一位社会学家解释说,这位院长一定得是一个好的榜样。“这话什么意思?”我问。好吧,未来的院长不仅必须拥有高学历文凭以及和学生相处融洽的能力,她还必须已婚,有孩子,外貌出众,衣着得体,积极参加社区工作等等。当时我断定自己是个糟透了的榜样。但话说回来,我并不想成为榜样。我想成为作家。一个人显然没有时间同时做这两件事。
用榜样的标准来评判未来院长或许将将还能勉强接受,但这也是文学评论家最喜欢的技巧之一,尤其是用来评价书中的女性角色,有时也用来评价女性作家本人,因此就必须对它做相当仔细地审视。我来举个例子:几年前,我读了一篇玛丽安·恩格尔《赫尼曼电影节》(2)的书评,是一位女性评论家写的。小说的主角是米恩,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她在书里花了很长时间追忆往事和抱怨眼前。她没有工作。也没有多少自尊心。她无病呻吟、自我放纵、充满内疚,对自己的孩子态度暧昧,对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场的丈夫也是如此。书评人对这一角色欠缺主动性,以及表面呈现的懒惰和没有条理表达了不满。她想要一个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角色,一个能够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女权运动开始呈现出来的理想女性形象更相符的角色。米恩没有被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榜样,这本书也因此减了分。
我自己的感受是,类似米恩这样的女性要比理想的女性多得多。书评人也许会同意,但也可能会说,通过描绘且只描绘米恩这一个形象——没有提供米恩之外的其他选择——作者是在对女性的天性作出陈述,而这种陈述只会强化原本已经过分显眼的米恩式不良品质。她想看成功的故事,不是失败的故事,而这对于小说作者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书写女性的时候,什么才算是成功?甚至成功有可能说得通吗?为什么,比如像乔治·艾略特,虽然她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女作家,却从未写过一个以成功女作家为主角的故事呢?为什么玛吉·托利弗非得因为她的叛逆而被溺死不可?为什么多萝西娅·布鲁克的理想主义无处施展,只能投注在两个男人身上,其中一个完全配不上,另一个又有点没头脑?为什么简·奥斯汀的角色们把聪明才智都用在挑选合适的男人而不是创作喜剧小说上?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这些小说将关注点放在通常会发生的,或者至少是能够落在读者认为可信范围之内的事情上;而作者也感到,自己身为女作家,实在太过特殊,因而缺乏可信度。在那个年代,女作家是异端,是怪人,是非常可疑的角色。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我留给你们自己去想,与此同时,让我引用几年前一位著名男性作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女诗人,”他说,“看起来总是鬼鬼祟祟的。她们知道自己是在侵犯男人的领地。”他接着又说了一句,大意是女性,包括女作家,只有一点好处,不过因为这次讲座是要发表的,我就不引用那句相当难以启齿的话了。
回到我的问题上来,对虚构女性角色的塑造……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谈。文学传统中并不缺少女性角色,小说家对女性看法的来源也和所有人一样:来自媒体,书籍、电影、广播、电视和报纸,来自家庭和学校,还有整体的文化,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见。另外,幸运的是,有时也来自与上述各项都相矛盾的个人经验。但我的假想主角可以选择许多文学祖先。比如,我可以谈谈民间传说中的老妖婆形象、德尔斐神谕、命运三女神、邪恶女巫、白女巫、白女神、财富女神,一头蛇发能把人变成石头的美杜莎、没有灵魂的美人鱼、没有舌头的小美人鱼、白雪公主,唱着歌谣的海妖、长着翅膀的鹰身女妖、有秘密或是没有秘密的斯芬克司,变成龙的女人、变成女人的龙,格伦德尔的母亲以及为什么她比格伦德尔更坏(3);可以讲讲恶毒的后母、可笑的岳母、仙女教母、缺乏母性的母亲、天生就适合做母亲的母亲,疯癫的母亲、杀害亲生骨肉的美狄亚、麦克白夫人和她的污点、夏娃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抚育一切生命的大海,还有耶稣说的“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也可以说说神奇女侠、女超人、蝙蝠少女、神奇玛丽、猫女以及赖德·哈格德拥有超能力和电动器官的“她”(4),普通凡人被她抱上一下就会丧命;又比如小马菲特小姐以及她和蜘蛛的故事(5),小红帽和她与大灰狼的不检点,安德洛墨达(6)被拴在岩石上,长发公主和她的高塔,披麻蒙灰的灰姑娘,美女与野兽,蓝胡子和他的各任妻子(只有最后一任除外),拉德克利夫女士(7)笔下受到迫害的纯洁少女逃避诱惑和杀害,简·爱逃离不当行为和罗切斯特先生,德伯家的苔丝遭人勾引又被抛弃;再比如《家中的天使》,手指向上的阿格尼丝,善良女性的救赎之爱,小耐儿在本世纪最虚伪的呜咽声中死去,小伊娃也遭遇类似的结局,让读者长舒一口气,疯言疯语的奥菲利亚沉入聒噪流淌的小溪,夏洛特姑娘带着生命的绝唱驶向卡姆洛特,菲尔丁的阿米莉娅在长达几百页的愁苦和凶险中抽泣,萨克雷的阿米莉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作者对她并没有那么同情。还比如欧罗巴与公牛交欢,丽达被迫与天鹅交媾,卢克莱西娅遭强奸受辱并随后自杀,多名女圣人奇迹般地逃脱被玷污的威胁,有关强奸的幻想以及它们与事实上的强奸有多么不同,男性杂志着重刊登金发美女和纳粹,还有从《坎特伯雷故事集》一直到T. S. 艾略特的性和暴力……以下我引用艾略特……“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曾经杀过一个女孩。任何男人都可能杀过一个女孩。任何一个男人都必然、需要、想要,在一生当中杀掉一个女孩。”还可以提一提巴比伦的淫妇,拥有一颗金子般心灵的妓女,恶女之爱,没有金子般心灵的妓女,《红字》,红衣女人,红舞鞋,包法利夫人和她追求的与陌生人激情缠绵,莫莉·布鲁姆(8)和她的夜壶还有她永远的“我愿意”,克里奥佩特拉和她的伙伴蝰蛇,这层关系让《孤女安妮》的故事有了新的含义。另外还有孤儿,莎乐美和施洗约翰的脑袋,朱迪思和霍洛芬斯的脑袋。还有纯爱杂志和它们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可惜的是,我既没有必需的时间也没有必要的知识,能以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探讨所有这些话题,它们也的确值得探讨。当然了,所有这些,都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来自西欧文学传统和它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变体。
除了我所提到的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变化形式,尽管西欧文学传统主要由男性塑造,但我所提到的女性形象绝不完全都是由男性所创造、传达和消费的。我提到她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读者可能遭遇到的女性角色的多样性,更是为了说明她们的多样性。对于女性的描写,尤其是男性所做的描写,绝不仅仅限于“孤独哭泣的人”(一个被动无助的人,不能行动只能受苦),直到十九世纪,这似乎都是主流哲学所鼓励的女性形象。但女性不止这一面,即便是刻板印象之下的女性,即便是在那个年代。
文学作品中女性固定形象的道德范畴似乎比男性角色更广。毕竟英雄和反派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两者都十分强大,都镇定自若,都采取行动并且面对后果。甚至连超自然的男性形象,上帝和魔鬼,也拥有许多同样的特点。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教授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单看装束和行动也很难区分哪个漫威漫画的超人是坏的,哪个是好的。麦克白,尽管不是一个多好的人,却也情有可原,再说了,要不是因为三女巫和麦克白夫人,他绝对也是不会下手的。三女巫的形象是一个典型例子。麦克白的动机是野心,那女巫的动机是什么呢?她们没有动机。就像石头或树木一样,她们仅仅只是存在而已:好的就纯粹的好,坏的就纯粹的坏。男性角色中最接近这种状态的就是伊阿古和海德先生了(9),但伊阿古至少部分是受到嫉妒所驱使,而海德先生的另一面则是充满人性的杰基尔博士。即使是恶魔也想获胜,但极端类型的女性形象似乎什么都不想要。海妖吃人,因为这就是海妖做的事情。D. H. 劳伦斯故事里那些蜘蛛似的恐怖老妇人——我尤其想到《处女与吉卜赛人》里的老太太——没有被赋予任何令人厌恶的动机,除了劳伦斯所谓的“女性意志”。麦克白杀人是因为他想成为国王,想获得权力,而三女巫则仅仅是在以女巫的方式行动。女巫,就像诗歌一样,不应有意义,只需要存在。追问这些角色的意义,还不如去问太阳为什么升起。
这种属于自然力量的品质,好或坏,这种物性的品质,最常出现在有关男性英雄的故事里,尤其是像奥德赛这样描述旅程的类型。在此类故事中,女性形象成为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事件,主角所参与的冒险。女性是静态的,英雄是动态的。他的经历和冒险在一片风景中展开,而这片风景是由女性和地理特征所组成。这一类的作品仍然非常普遍,任何读过詹姆斯·邦德系列、亨利·米勒,或者更加本土的罗伯特·克罗奇《马头人》的读者都可以作证。类似的女性文学探险形象则凤毛麟角。或许可以将她们称为女冒险家,仅仅是这个词语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就说明了她们与男性类型的不同。一个列出一连串女人的男人,比如唐璜,或许会被看作流氓,但却是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流氓,而女性角色,从摩尔·弗兰德斯到埃丽卡·容《怕飞》中的伊莎多拉·温,却不能在没有大量解释、痛苦和内疚的情况下做同样的事。
我已经提到了“孤独哭泣的人”,被动的女性受害者,承受所发生的一切,唯一的行为就是逃避。也有相似类型的男性角色,但通常都是儿童,比如狄更斯笔下的保罗·董贝(10)、雾都孤儿,以及多特寄宿学校里受苦受难的学生们。要让成年男性表现出这些特质——恐惧、无法采取行动、感到极其无能为力、泪眼汪汪、觉得陷入困境和无助——他就必须是个疯子或者是少数群体的一员。这种感受通常被视为对男性本质的违背,而同样的感受在女性角色身上则会被当作是对天性的表达。被动无助的男人是非典型的异类;被动的女人则在标准范围之内。虽然强大的、或者至少是积极的英雄和反派都被视为人类理想的实现;但强有力的女性,文学世界中有很多,却通常都会被加上超自然的光环。她们是女巫、神奇女侠或是格伦德尔的母亲。她们是怪物。她们并不完全是人类。格伦德尔的母亲比格伦德尔更坏,因为她被看作是对标准形象更加严重的背离。格伦德尔,说到底不过是又一个贝奥武夫,只是更庞大也更饥饿。
但假如说,我希望塑造一个女性形象,并非自然力量,无论善恶;也不是被动的“孤独哭泣的人”;她能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引起也承受各类事件,或许甚至还有一些野心,一些创造力。我的文化里有什么故事能给我讲讲这样的女性呢?在公立学校层面并没有多少,这多半也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迪克与珍妮,虽然对于书里的帕芙和斯波特还有些模糊的印象(11)。但在校外,有漫画书:蝙蝠侠与罗宾,超人(还有路易斯·莱恩,那个永远傻傻等待被救的人),霹雳火和佐罗还有其他许多许多,都是男性。当然了,也有神奇女侠。神奇女侠是亚马孙的公主,和其他亚马孙人一起生活在一座岛上,但是岛上没有男人。她有能挡子弹的神奇手镯,一架隐形飞机,还有魔法套索和超人的本领和力量。她打击犯罪。只有一个问题——她有个男朋友。但是,假如他吻了她,她就会像剃去须发的参孙一样失去所有的超凡神力。神奇女侠始终没有结婚,一直都是神奇女侠。
然后还有《红菱艳》——不是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的童话,而是一部电影,主演是莫伊拉·希勒,有一头漂亮的红头发。整整一代的女孩子都被带去看这部电影,作为生日派对的特别节目。莫伊拉·希勒是一位著名的舞者,然而可惜的是她爱上了乐队的指挥,这位指挥,出于某种当时令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禁止她在婚后跳舞。这道禁律让她非常苦闷。她想要这个男人,但她也想要跳舞,这个矛盾最终让她一跃跳向迎面驶来的火车。主题思想非常清晰。艺术生涯和好男人的爱两者不可兼得,如果尝试,最后只会以自杀收场。
另外还有罗伯特·格雷夫斯(12)的诗意理论,在他的许多书里都有阐释,尤其是我十九岁时读的《白色女神》。对格雷夫斯而言,男性行动,而女性只是存在。男性是诗人,女性是缪斯,是白色女神本身,启迪人心却又最终毁灭一切。那么想成为诗人的女性又如何呢?这也是可能的,但这位女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白色女神,作为她的化身和喉舌,很可能也要像她一样实施破坏。格雷夫斯为女性艺术家提供的模式不是“创造然后被毁灭”,而是“创造然后毁灭”。比跳轨自杀稍微更有吸引力一点,但也差不太多。当然,你总是可以忘了这一切,安顿下来,去生孩子。看起来似乎是一条更加安全的路,而这毫无疑问是整个文化所给出的信息。
但社会所提供的最为耸人听闻的警世故事,莫过于真实女作家的生平本身。女作家无法被文学历史所忽视;至少是十九世纪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米莉·迪金森,以及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地位太过重要,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她们的传记作者绝对可以强调这些女作家的古怪和反常,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简·奥斯汀终身未婚。艾米莉·勃朗特也是,而且很早就去世了。夏洛蒂·勃朗特死于分娩。乔治·艾略特和一个男人未婚同居,没有生育任何孩子。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透过裹尸布上的蛀洞观察生活”。艾米莉·迪金森闭门不出,而且很可能是个疯子。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倒是成功地挤出了一个孩子,但并没有好好把他养大,还沉迷于降神会。这些女性是作家,没错,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并不是女人,或者说即便是女人,她们也不是好女人。她们是不好的榜样,或者说她们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暗示的。
“以前我有个男朋友,他管我叫惊奇女侠。”女巫希尔达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连环漫画里说。
“因为你强大、勇敢还很真诚?”山精问。
“不是,因为他对我很惊奇,不确定我究竟是不是个女人。”
如果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表现优秀,漫画告诉我们,就必然要牺牲你的女性气质。如果想有女性魅力,就必须把舌头拔了,像小美人鱼一样。
确实,关于埃德加·爱伦·坡的酗酒成性、拜伦的乱伦、济慈的肺结核,还有雪莱的不道德行为也有很多议论,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浪漫的反叛不但让男性诗人更令人感兴趣,也让他们更有男人味。很少有人提到,两个艾米莉、简、克里斯蒂娜和其他女作家以她们的方式生活,是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获得写作的时间,并养成写作的专注力。十九世纪女作家令人称奇之处不是她们数量稀少,而是她们竟然真的存在。如果你以为这种现象已经烟消云散,就去读一读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占卜者》。中心角色是一个成功的女作家,但她显然意识到,自己不能既写书又同时留住一个好男人的爱。她选择了写作,朝那个男人扔去了一只烟灰缸,在书结尾的时候她一个人生活。作家,无论男女,都必须自私,只是为了得到写作的时间,但女性并没有被培养出自私的品质。
关于创作才能的风险,更加极端的版本来自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的自杀,以及她们获得的病态关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不但被看成怪异且缺乏女性气质的人,更被视为注定走向毁灭。通过自己的人生或是自己创作的角色,把孑然一身或者难逃失败的形象演出来,确实相当具有吸引力。万幸,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被逼急了,我们总还是可以想想盖斯凯尔夫人,哈里特·比彻·斯托,甚或是,比如说,艾丽丝·门罗和阿黛尔·怀斯曼,还有其他许多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她们似乎能够同时兼顾为人妻、为人母和写作,与这个文化里的其他人相比也没有变得明显残缺畸形。
但《红菱艳》现象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女作家在这个社会的处境确实要比男性作家更艰难。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与生俱来、难以理解的生理或是精神层面的不同:困难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这些刻板印象仍然在周围埋伏,随时准备以完整的形态从男女批评家的脑中一跃而出,缠住毫无防备从身边经过的角色或是作者。在道德层面上,对女性的要求依然是她们要比男性更优秀,甚至连女性自己,甚至连女性运动的一些分支也这样认为;假如她们不是天使,假如她们身上刚好存在普通人的不足,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尤其是假如她们表现出任何优势或者才能,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其他方面,那她们就不仅仅是普通人,而是还不如普通人。她们是女巫、美杜莎,是毁灭性的、强大的、可怕的怪兽。有粉刺和瑕疵的天使不会被看作凡人,而会被看作魔鬼。一个像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所表现的一样反复无常的角色不是可信的创作产物,而是对女性天性的一种诋毁,或者一种说教,说的不是人性的弱点,而是所有女性特有的比脆弱更脆弱的缺点。女性依旧承受着许多社会压力,要做到尽善尽美,而假如她们以除最严格指定方式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式靠近这一目标,则又会招致许多怨恨。
读一读我自己的资料夹就能很轻易地举例说明:我可以给你们讲讲巫师玛格丽特,美杜莎玛格丽特,吃男人的玛格丽特,抓着许多不幸男人的尸体一步步爬向成功。渴望权力的希特勒玛格丽特,怀抱她占领整个加拿大文学领域的狂妄计划。必须阻止这个女人!所有这些传说中的生物都是批评家的创造;这些批评家并不都是男性。(还没有人把我称为天使,但殉道者玛格丽特肯定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尤其是假如我年纪轻轻就死于车祸的话。)
继续摘录下去会相当有趣,但也会显得相当刻薄,考虑到其中有些肇事者就算不在观众席里,也是这所大学的雇员。所以相反地,让我发起一份简单的呼吁;女性,无论作为虚构形象还是作为人,都必须被允许拥有不完美之处。假如我要塑造一个女性角色,我会希望能够展示她拥有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情绪——憎恶、嫉妒、怨恨、欲望、愤怒和恐惧,同时还有爱意、怜悯、宽容和喜悦——而不必让她被宣称为怪物、污点,或是不良的榜样。如果情节需要的话,我同样也希望她精明、睿智和狡黠,而不用让她被贴上物质女神的标签,或是成为表现女性阴险狡诈昭然若揭的典型例子。很长时间以来,文学作品中的男性一直被视为个体,而女性则只是一个性别的代表;或许是时候把大写的“女”字从“女性”一词中除去了。我自己从来都不认识什么天使、鹰身女妖、女巫或是大地之母。我认识一些真实的女性,她们并不都比男人更友好、更高尚、受了更长时间的苦,也不一定都不如男人那么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描写她们的故事正日渐变得可行,尽管和往常一样,我们还是难以区分哪些是自己实际看到的,哪些是教育引导我们看到的。谁知道呢?甚至我自己评价起女性来也可能比评价男性更严厉;毕竟,她们要为原罪负责,至少这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
让我用阿格尼斯·麦克菲尔的话来结尾,她虽然不是作家,但对于至少一种文学刻板印象却十分熟悉。“听到男人说起女性是家中天使的时候,我总会,至少是在心里,怀疑地耸耸肩。我不想当家里的天使。我自己想要的也是我想让其他女性得到的:绝对的平等。在达成这一点之后,男人和女人可以轮流当天使。”我会换一种方式来说:“男人和女人可以轮流当一个普通人,活出每一个人的丰富个性和变化万千。”
(1)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文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本书中译注均为脚注。原作者注均为篇尾注。
(2) 玛丽安·恩格尔(Marian Engel,1933—1985),加拿大小说家,代表作《熊》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3) 格伦德尔(Grendel)是英国叙事诗《贝奥武夫》中记述的巨人怪物,他的母亲是一个女妖,也是主人公遇到的第二个敌人。
(4) 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小说家,以写非洲的冒险故事闻名,尤以《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她》(1887)最为著名。《她》讲述了剑桥大学教授霍利和他的养子利奥去非洲湮没的克尔国探秘,内容涉及到利奥的一名叫卡利克拉提斯的先祖,此人是两千年前埃及的一个祭司,不知为何,被当时克尔国的至高无上的白人女王“她”——艾莎杀害。霍利和利奥穿过许多危险的区域,最终找到集权势、美丽、残暴于一身的“她”。
(5) 《小马菲特小姐》是一首经典英语童谣,讲的是小马菲特小姐在森林野餐时遇到了一只蜘蛛,进而发生了一场小小森林冒险的故事。
(6)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因母亲不断炫耀她的美丽而得罪了海神波塞冬之妻安菲特里忒,被父母用铁索锁在刻托经过路上的一块礁石上,后为宙斯之子珀耳修斯所救,成为仙女座。
(7) 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英国女小说家,以写浪漫主义的哥特小说见长。被称为“第一位写虚构浪漫主义小说的女诗人”。
(8) 《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妻子。
(9) 伊阿古是莎士比亚《奥塞罗》剧中的反面人物。海德是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中的主人公,也是文学史上首位双重人格形象,即下文中的杰基尔博士。
(10) 《董贝父子》是狄更斯发表于1848年的长篇小说,保罗是商人董贝的儿子。
(11) 经典英语早教绘本中的儿童角色,帕芙和斯波特是其中的猫和狗。
(12)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