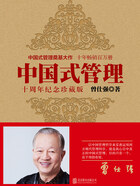
第二节
把二看成三才能跳出二分法的陷阱
现代人的思维法则,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采用“二分法”。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再从中选择其一作为答案。看起来清楚、明确,好像是非十分明白,而且简单明了。
例如唯心、唯物的争论,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结果产生“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不同的主张(见图2-2)。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那么不是唯心论者,便成为唯物论者。

图2-2 二分法的思维
西方的管理沿用这种思维法则,把人“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将管理的方式划“分”为人治和法治(见图2-3)。
中国人的思维法则本来不应该如此。由于太极的启示,中国人擅长在“一分为二”的分析之后,“把二看成三”,在相对的两端找出中间的灰色带,也就是二“合”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形成第三个概念(见图2-4)。

图2-3 二分法的应用

图2-4 太极的思维
例如唯心、唯物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中国人看出两个之外的第三个概念,叫作“心物合一”,因而统合了唯心和唯物成为“心物合一论”。
中国式管理承袭太极思维法则,把人看成三种。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
至于管理的气氛,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却十分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说起来实施法治,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见图2-5)。
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长久以来成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借口。西方人重“分”,喜欢用分析法,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离破碎。专业化的结果,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个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

图2-5 太极思维的运用
中国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设法避免?一分为二之后,当然可以二合为一。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说:“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见图2-6及图2-7)。

图2-6 对也会推成错

图2-7 事情像是圆的
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即把“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看成三个。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个“无可无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跟着鄙视起来。
中国式管理依据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凡是两个概念都能看出三个,无形中又多了一种选择,所以弹性更大、包容性更强,其实就是“合”的效果(见图2-8)。

图2-8 把二看成三
例如西方劳资对立,员工是劳方,资本家是资方,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协议,更不容易建立共识。各说各话,划“分”出不同的立场,然后讨价还价才勉强和解,但是其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劳资之外,看出一种“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尽量采取间接方式,通过干部的承转,养成习惯之后,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通过干部,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比较容易化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劳方遇有问题,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弄得老板不像老板,失去应有的尊严,干脆一气之下关门不当老板,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
有问题必须解决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西方一分为二,问题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种选择(见图2-9)。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尽职、有担当,而不解决的视为不负责、不尽职、缺乏担当。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决不行,问题一直持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恶化,以致无法解决,或者更加花费成本。但是解决也不行,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势必引起其他问题,甚至爆发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岂不悔恨已晚?

图2-9 二选一
在解决和不解决之道中,有一条“合”的途径,称为“化解”(见图2-10)。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无形中既“解决问题”,又避免后遗症,或者把它减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国人的太极功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化解掉,化到好像没有问题要解决,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实力。

图2-10 二合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没有办法,摆脱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称为“必要的罪恶”。
中国人讲阴阳,很简单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轻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碍。
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的不同变化。阴可以变阳,阳也能够变阴,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使得宇宙万象时刻都在变易,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不一定”的观点。“不一定”如果和“一定”相对峙,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因此中国人的“不一定”,实际上包含了“一定”在内,而一定的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可能性。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其性质也相当不一定。
有一位老板很热心地自己开车送笔者回新竹。那一天我们在车上谈了很多问题,快到新竹的时候,他问:“究竟是运气重要,还是努力要紧?”
笔者回答:“当然运气要紧。”
他非常高兴,接着说:“果然如此,运气好的时候,好像挡都挡不住;运气不好时,再努力也没有用。”
笔者又说:“但是,不努力怎么证明运气好不好?所以还是努力比较重要。”
他刚开始愣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起来:“对!对!努力和运气两样都重要,不努力不知道运气好不好,运气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中国人的《易经》素养,毕竟随时可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
当前社会上的万般乱象,说穿了不过是“二分法”同《易经》的“三分法”之争。
“二分法”的主张,是非必须明确,一切都要透明化,大家把话说清楚,并且把这些作风当作现代化的指标,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谈现代化。
“三分法”则认为“真理往往不在二者之一”,是非当然要明确。但是人不是神仙,怎么能够分辨得十分正确,一切是非,不过是自圆其说,常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阵子的是,很快就会变成非,怎么可以草率地论定呢?何况“真理在二者之中”,是非中间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既非“是”也非“非”,既有“是”,也有“非”,难道可以轻易地忽略掉吗?
是非难明,并不表示是非不明。在是非尚未明确化之前,又怎么能够不顾一切地透明化呢?大家就算有心把话说清楚,也得顾及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言语的局限性,根本就说不清楚,又该怎么办?
其实,现代化的西方,也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他们正努力地提倡后现代主义,希望以三分法来代替僵化的二分法。可惜许多人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接近《易经》的三分法,否则也就不会花费那么多心力,来做无谓的抗争了。
二分法毕竟比较简单易学,而且条理分明、结果十分明确,符合大多数不喜欢动脑筋或者不会动脑筋的人,所以拥护者不在少数。
三分法不但复杂难懂,而且采取圆周式思考法,结果又不明确,难怪很多人大伤脑筋。不是不喜欢它,便是错用了它,无论过与不及,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过去大家比较客气,不敢自我膨胀,也不敢过分武断,虽然也是二分法和三分法明争暗斗的局面,却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无事。现代自由民主,大家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不但自我膨胀,而且十分武断,二分法和三分法还没有搞清楚,便抓住麦克风不放,反正说错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会脸红呢?
现在和过去,都是阴阳消长的变易。换句话说,都在明争暗斗。所不同的,不过是过去明少暗多,而现代明的成分多、暗的成分比较少而已。
看清楚三分法的人,对事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看起来有点冷漠,实际上十分理智。只知道二分法的人,凡事很快就要分辨是非、对错、善恶,越热心就越容易情绪化,看起来很有正义感,其实非常冲动。还有一种看不懂三分法的人,误以为三分法便是一切走中间路线,扮演骑墙派的角色,随时靠左、靠右,自认为是左右逢源,不料却成为投机取巧的小人。
整个社会,被这三种人搞得昏天暗地,以致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公论:任何新闻,都出现相反的论证;一切活动,都具有正反不同的看法。美其名曰多元化,实际上是乱七八糟。
中国人讲不讲理?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道理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生气的时候经常很不讲理,甚至恶劣到蛮不讲理的地步。偏偏中国人的情绪浮动得相当厉害,常常生气,所以显得十分不讲理。
这样说起来,中国人究竟是讲理的,还是不讲理的?答案应该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很难讲”。
很难讲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在“讲理”和“不讲理”两者之间,选择其中之一。否则的话,为什么很难讲呢?采取三分法的思维方式,把“讲理”和“不讲理”两者合起来看,形成“情绪稳定时很讲理而情绪不稳定时十分不讲理”的第三种情况。由此可见,情绪稳定与否对中国式管理非常重要。管理以“安人”为目的,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安定大家的情绪呢?先把情绪稳定下来,然后才从事管理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是修己安人的深一层内涵。情绪管理对中国人十分重要,不能够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