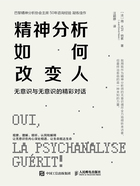
导读
在内心深处的相遇,让治愈发生
心理咨询是如何改变人的?治愈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精神分析的长程治疗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是否还有其治疗意义?这是很多来访者在想要进行心理咨询或心理分析时常见的心理困惑。
法国巴黎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简-大卫·纳索在《精神分析如何改变人:无意识与无意识的精彩对话》这本书中,将自己近50年的心理咨询临床经验呈现在读者面前,用清晰且结构化的表达,告诉读者分析性的治疗是如何作用于来访者的,让我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需要掌握的相关理论繁多而复杂,需要阅读的文献也非常晦涩难懂,并且很多人在学习训练初期也很难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我看来理论与实践需要反复交叉验证,最终才会融入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人格,在其与来访者的无意识工作中被见证。
简-大卫·纳索的这部著作却给了我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让我认识到原来精神分析也可以按照某种结构去操作,即他在书中提到的精神分析的五步法。这五步可以帮助心理咨询师抵达来访者的无意识,最终通过解释修复创伤,让来访者获得治愈与修通。
简-大卫·纳索提出精神分析师要使用“工具性的无意识”,这让我想起我在接受精神分析培训时,曾奇峰老师曾说,真正成功的治疗,除了治疗设置、治疗技术,其实最关键的起效因子是治疗师(后称精神分析师)这个角色。精神分析师本身就是一个“工具”,作为一种“容器”,一种可以给予来访者温暖、稳定的存在,他的倾听的态度、不含诱惑的深情、不带敌意的坚决,在有保护的空间里,让爱与恨浮出无意识的海洋。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是让生命抵达生命。
精神分析中的倾听是在听什么?是来访者的情感冲突、内在需要、愿望及梦,是从精神分析师的无意识走向来访者的无意识,让来访者的无意识走向精神分析师的无意识。那么,如何去倾听?简-大卫·纳索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个共分五步的过程:观察、理解、倾听本身、认同幻想中孩子的情绪、解释。在这篇导读中,我也想尝试结合自身的经验,带领大家去感受精神分析的艺术与魅力。
从来访者走进咨询室的那一刻开始,精神分析就已经开始了:来访者会带来哪些无意识的语言呢?他的表情是紧张慌乱的、麻木的,还是悲伤的?身体是僵硬的,还是放松的?是素颜的还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头发是凌乱的还是整洁的?他的坐姿是前倾的,还是靠后的?态度是有点挑衅的,还是讨好的?他在进行目光交流时是大方的,还是躲闪的?他的穿着打扮是与他的年龄身份相符的,还是不太一致的?他的声音是低沉的还是亢奋的?这些既是来访者给精神分析师的印象,也是精神分析师透过分析的眼光观察到的。从这些观察到的素材中,精神分析师已经开始对来访者做出某种假设,并且带着假设与疑问展开与来访者的对话。
来访者的这些非语言信息是其内在心理现象的延伸。比如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在第一次到咨询室时穿着不太合身的深绿色西装,看起来有几分老成;而在谈恋爱的阶段,她会穿超短裙,打扮得很青春;在跳槽成为部门主管后,她的穿着变得更有品位且职业化;在开始一段真正稳定的亲密关系后,她的穿着开始变得更有女人味,但又透着干练。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都可以成为被分析的内容,深绿色或许意味着特别压抑、生活没有色彩,青春的装扮是为了迎合男友的喜好,在升职后她则变得更为独立,等等。我带着好奇,与来访者一起探索她的内在,也在同时观察我自己的内在世界,比如我是否喜欢她的变化,她想要在我面前表达什么?这就是第二步——理解。
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步——倾听本身。倾听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倾听外在,即来访者表达了什么;二是倾听内在,即我听见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比如一个女性来访者因为丈夫出轨来寻求帮助,她发现自己投入那么多心血经营的令人羡慕的“美好”家庭原来都只是幻象,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很可笑。此时我会听到她内心的冲突。一方面,家庭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她坚守的东西被摧毁了,她的人生投资在这一刻似乎一下子归零了;另一方面,似乎这段关系中也曾经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时她又因为沉没成本有着非常多的不甘心。另外,她还有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等。她渴望回到过去夫妻俩无话不谈的生活状态,希望自己能变得坚强,可以挺过这场危机。她当下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与处理这段关系,是选择离开还是共同面对、重建信任等。我还可以倾听到她的情感内容,有惋惜、懊悔,也有难过、羞耻、愤怒、无助、怨恨等。精神分析师把这些听到的内容,用来访者的语言表述出来,帮助来访者发现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容,从而从混乱与无序中走出来,进而做出某些改变。
精神分析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母婴关系,而实际上,在咨询室中同时存在三种平行关系:来访者现实生活中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客体关系(来访者在早年与重要客体的关系)。精神分析师在咨询中的移情与反移情,就是在体验来访者的内在客体关系以及被来访者激活的自己的内在关系与冲突。被充分分析过的精神分析师,有能力在这些复杂的情感中区分哪些内容是来访者自己的,哪些内容是来访者给分析师带来的。精神分析师作为理想化的母亲对幻想中的孩子的情绪进行认同,这就是倾听的第四步。
创伤发生在过去,来访者也因此被固着在过去。精神分析师可以陪着来访者重新回到创伤的发生地去见证,去与来访者一起体验那些痛苦的情绪。此时,来访者不再恐惧,因为他所经历的痛苦被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见证、支持、理解与共情,他有了与早年经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此时领悟与修通才成为可能。
在此时此地,我会给予来访者解释,或者叫诠释,这是精神分析的精髓,也是最难的部分。因为只有在观察、理解、倾听、共情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解释。如果精神分析师过早或过快地给出解释,来访者就很难有所领悟,或者会否认解释。还有一种情况是解释不到位,来访者的无意识无法接受或不认同。当然,精神分析师的很多解释只是一种可能性,越表达不确定,越能引发来访者的自由联想。在我看来,这也是可分析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容纳那些天马行空的无意识内容。有时精神分析师需要小心翼翼地与来访者共同寻找解释的正确方向,就像在投石问路。这样双方可以就同一问题从不同方向做出解释,不断地澄清、面质,从而将混乱的无意识内容变得更有逻辑性、更结构化、更加清晰。
简-大卫·纳索认为“解释是不断收割无意识成熟的果实”,他把解释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说明性解释,另一类是创造性解释。
说明性解释是思索的结果,它的目的是清楚地传达来访者模糊知道的事情。比如来访者带着生活中的混乱来到咨询室,只是感到痛苦,却并不清楚令他痛苦的究竟是什么。有的来访者可能只是需要精神分析师的在场与陪伴,需要感到安全,这样他就可以展开自我分析,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过程中,其思路就会越来越清晰。当然,精神分析师可能内心已经有了某些解释,但如果能够让来访者自己去表达,其领悟可能会更深刻,也会产生更大的改变。
说明性解释会将来访者当下的痛苦和冲突与过去关联,让来访者以联系、连续、发展的眼光了解自己,并且将那些被来访者忽略、忽视或逃避的内容以某种方式呈现。用于解释、分析的素材往往来自来访者那些不自主的表现,包括自动化的思维、无意识内容、病理性的表现,以及可转移的情感,也就是移情表现,等等。
简-大卫·纳索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阐述创造性解释的精妙之处。创造性解释包括叙述性解释、拟人性解释、动作性解释以及主观性纠正(或者叫纠正性解释)四种新变体。接下来,我会结合我与来访者一起工作的经验,用更让中国人感到熟悉的语境展开解释这四种新变体。
叙述性解释就是通过故事或隐喻的方式帮助来访者理解其内心世界。比如有位女性来访者讲到了自己的焦虑,她说自己每天恨不得把每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只要浪费了时间,她内心就极度不安,她不能允许自己停下来。我向她讲了一个“无足鸟”的隐喻,这种鸟会耗尽一生一直飞行,一辈子都不会停下来,它一生只能停止飞行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而这位来访者就像那只“无足鸟”,不能让自己停下来。听到这个解释,来访者感觉它非常贴切地反映了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
她在谈到亲密关系时,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分离焦虑,她尤其害怕男友在她睡着时离开。她对男友说,如果早上他要去上班时自己还在熟睡,一定要叫醒她。来访者讲述了她小时候被送到姥姥家的故事。当时母亲只能一个月来看她一次,因为害怕她哭闹,每次走的时候都是等她睡着后悄悄地离开。在这个故事中我会帮助她把那些未被表达的情感补充进去:当你醒来,发现妈妈不见了,你感到非常害怕,会想“妈妈怎么就消失了”“她还会回来吗”,你多么渴望在妈妈温暖的怀抱中再多待一会儿,再闻闻妈妈身上的味道,听听她的喃喃细语。你哭喊着找妈妈,姥姥努力哄你,告诉你妈妈还会回来……
拟人性解释则会用拟人化的表达呈现来访者的内心世界。曾经有一位女性来访者在咨询中提到了她的那只猫:她情绪不好时就会对猫发脾气,猫则会出于报复在家里的床上、沙发上撒尿,这让她很伤心。当她尝试体会猫的感受时,她说,猫也会感到委屈,被这样粗暴地对待也会很难过,她开始变得更有耐心。当她能够善待猫的时候,她也就学会了如何善待自己。
另外,在与来访者开展与“梦”相关的工作时,我会采用一种自居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拟人性解释。什么是“自居”,就是回到梦境中,把自己当作梦中出现的某个无生命的东西,尝试说出它想要说的内容。梦中出现的所有人或物都是人心灵世界的影子,都与自己有关。比如,你的梦中出现了一个枯井,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枯井想要说些什么?它可能会说,自己的内在多么干涸、匮乏,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是被人遗忘、遗弃的,是孤独、寂寞的,在等待着被充盈,等等。
在使用拟人性解释时,我会向来访者表达认同,向他的内在小孩表达认同,或者向他的重要养育人表达认同,并且用他们的语言进行解释。这也会扩展来访者的视角,让其感觉曾经遭受的痛苦被人理解,或者换个角度,看到当年父母的不容易及局限性,甚至可以帮助当年受过伤害的孩子表达对父母的愤怒等。
动作性解释其实在很多心理治疗技术中都有广泛应用,所以说精神分析是大多数心理治疗技术的源头。在家庭治疗中,精神分析师也会使用家庭雕塑来呈现来访者的关系模式:他愿意离谁更近一些,离谁更远一些,他愿意面对这个人还是背对这个人,他的感受是什么,此时他想对这个人说些什么,等等。家庭治疗师萨提亚女士提到的四种不良的沟通姿态,用身体雕塑来呈现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模式,通过身体动作来感受和体会指责、讨好、超理智、打岔等沟通姿态体现的问题。当然,戏剧治疗、舞动治疗等都是透过行动进行创造性解释。
精神分析师通常都是基于假设给出解释,解释中会有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而在分析过程中,最可怕的是精神分析师表现出来的确定感,这往往是精神分析师的自恋的表现。分析给出的解释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给来访者带来不同的体验,同时也会给来访者带来不一样的视角。解释是否正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来访者的反应,精神分析师所做出的纠正性解释。在认知层面,精神分析师可能会通过纠正性解释挑战来访者某些固化的思维、不合理的信念,比如来访者认为自己患抑郁症是羞耻的,父母对我再不好我也不应该恨他们,等等。这些限制性想法来自超我[1]的束缚,它会压抑人的内在需要与情感,让人极度不自由。
每个来访者都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师需要在每一步的咨询中全身心地投入、倾听与交流。除了上面所提到倾听与解释的方法,想要成为精神分析师还需要具备怎样的特征呢?简-大卫·纳索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保持纯真。
第二,保有感到好奇的能力。
第三,不要被日常的惯性打败而变得麻木。
这三点让我明白,怪不得我所接触的很多精神分析师会给我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他们大多有3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却经常在严肃的督导或案例讨论中透露出某种孩童般的天真,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对那些正经历苦难的人饱含深情,充满慈悲的力量,用生命温暖、治愈在人生旅途中相遇的每一个受伤的灵魂。
任丽
动力取向心理咨询师
《我们内在的防御:日常心理伤害的应对方法》一书作者
[1]人格结构中,由自我分化而来的、道德化了的、代表社会和文化规范的人格部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