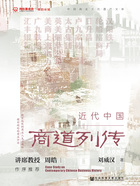
三 制度不善,濒临破产
1890年,这家中国官办钢铁企业,前后花费了600多万两白银,从西方购置了全套设备,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然而,这样耗资巨大、规模庞大的钢铁厂,从成立到亏损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实在是让人咋舌。这样的挫败与它不适当的管理经营制度有着直接关系。
(一)同时期美国钢铁企业的发展[17]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后便开始发展钢铁行业。美国却晚了几乎一个世纪,它的钢铁业在19世纪60年代才逐渐起步,在时间上与中国同时期的洋务运动相一致。中美两国的钢铁行业可谓是同时期发展,但是经过短短30年的时间,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汉阳铁厂几乎破产,即使全力挽救,之后也只能逐渐成为日本钢铁企业的代工厂。民国初年,盛宣怀再度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先后与日本制铁签订协议来筹措基建资金,最后却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拱手让人了,致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盛宣怀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因为请袁世凯出山,以及被各方谴责他的四川收路政策导致动乱等,被革职后逃亡日本,之后他便一再出现代理人问题。他急于重出江湖,被日本人抓住了这根软肋,日本以协助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为由,借由大举借款的手段,最后就把汉冶萍公司给抢走了。但是,美国的卡耐基钢铁公司却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须知,当时的美国政府可是没有给卡耐基钢铁公司任何优惠政策或是特别待遇的。
说起卡耐基,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管理哲学,或者是他那由贫民窟到世界首富的传奇人生。他之所以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是因为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哲学正确地运用于自己所建立的钢铁帝国——卡耐基钢铁公司,这家百年企业现在依旧屹立于世。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于1835年出生在苏格兰一个贫民家庭,受英国的饥荒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童年时便与父母移民美国。由于家庭贫困,为了糊口,他14岁便去纺织厂打工,之后还相继做过锅炉工和邮递员。在送电报的两年里,卡耐基白天工作,晚上去夜校读书,学习复式记账法,他坚信这种知识在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收发电报的技术。命运之神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电报机的使用和各种电报代码的卡耐基,在他18岁的时候,被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西部分局局长托马斯·斯科特雇用,担任他的私人报务员。此后,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十余年里,卡耐基平步青云,同时从实践中掌握了铁路公司的管理、会计、组织和控制等现代化大企业的整套体制和管理技巧,为之后开创自己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65年,卡耐基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辞职之后,创办了匹兹堡钢轨公司、机车制造厂以及炼铁厂。这个时期的美国钢铁行业,虽然受到了欧洲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影响,但是还处于分散经营的阶段。这里所说的分散经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行业中存在许多小型规模的炼铁厂,而是将从铁矿石到铁制品的制作环节分割开来,进行专精分工,让不同的厂家负责生产中的不同环节。但是这种“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非常容易产生溢价,即中间商对上一个环节的产品加价之后,再卖给下一环节的厂商,这样一来,便会大大提高钢铁制品的成本。看到这一缺陷的卡耐基,果断决定成立一家综合的、囊括了钢铁整个生产过程(包括原料供给、钢铁生产和销售)的现代钢铁公司,又运用之前在铁路公司学习并实践的一体化经营理念,结合当时最先进的贝塞麦炼钢法(the Bessemer Process)和西门子-马丁敞炉炼解法(the Siemens-Martin Process)进行钢铁制品的产销活动。
高楼大厦平地起,许多企业都曾经历过开创摸索的阶段。当时美国的许多企业在财务上都实行简单记账法,而钢铁行业中的企业由于分散经营,几乎不会进行会计核算,只是简单粗暴地按照总产量来分摊全部费用,从而决定利润的多少。这种做法的最大问题便是坏账、死账一大堆,而且根本无法清晰地界定成本、销售额和真实的利润,更别说以此为依据,进行企业的生产管理改革。但是当时市场需求旺盛,绝大部分的业主乐得赚取小钱小利,并不急于思索精进。这时,卡耐基年轻时在夜校学习的复式记账法,帮助他建立了企业的财政制度——成本会计,可以帮助确定产品的价格,不但使得定价可以低于行业中其他的竞争者,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在市场,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另外,运用成本会计法,可以精算成本、产量与利润的实况,以及剖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和经营策略,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18]。
更甚者,卡耐基自身的职业经历,烧过锅炉,发过电报,又在铁路公司工作十余年,这些工种都与钢铁打交道,使他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已了然于胸。所以当他成立了自己的钢铁公司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合钢铁生产的程序,实行一体化的生产。卡耐基以使用贝塞麦转炉为契机,实现了钢铁的“一条龙”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之后,卡耐基又整合了钢铁原料的供应渠道,收购了一些距钢铁厂较近的矿场和煤场,从而保证了原材料能够持续稳定地供应。在充分调研了市场需求,了解了钢铁制品的销路及销量之后,为了能够更快、更多地生产,卡耐基又采购了适合的平炉和炼焦炉。企业最开始生产一吨钢的成本是56美元,而到1900年,每吨钢的成本便下降到11.5美元,这不能不让人钦佩卡耐基的管理能力。他结合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学习到的企业管理方法,建立了钢铁厂相应的人事考核制度,恰当地分配了企业管理权,并明确了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此一个有序、高效的钢铁厂的成果绝非侥幸,正如《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说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卡耐基正面看待人生经历,他从不错过学习的机会,更是将所学运用到他事业的方方面面,终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卡耐基将技术与管理相结合,至1900年,他的钢铁公司不仅是美国最大的,更是世界上钢铁产销量最大的。反观与它同时期的、号称“亚洲最大钢铁企业”的汉阳铁厂,当时却在依靠着外国借款艰难度日,可谓举步维艰,虽有朝廷的大力支持,却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汉阳铁厂弊病丛生的管理模式[19]
在1896年盛宣怀接手之前,汉阳铁厂是个官办企业。所谓官办企业,类似于现在的国有企业,其所有权归属于国家。但是汉阳铁厂相较于现在的国有企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管理者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换言之,就是国家出资,由实业经理人来全盘经营。如此看似尊重企业经营事业,但其实结果并非如此。自1890年汉阳铁厂成立以来,张之洞就被批评大权独揽。他对企业有着绝对控制权,是企业的最终决策者,任何关于经费的使用、管理人员的任免等企业管理方面的事项都全凭他的个人意志来决定。准确地说,汉阳铁厂打从一开始就主要被当作政治山头来看待,所以首要任务就是壮大自己的队伍。建厂初期,张之洞采用衙门式的管理人员遴选方法,在将传统政治人脉关系作为用人原则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好恶,选取管理人员,被选中的管理人员几乎全部是他自己的亲信。当时的政治风气就是如此,毕竟这样的大规模创新工程不找自己人来帮忙怎么会放心呢?况且,李鸿章也是不遑多让,同样大举安插自己的人马。但是,李鸿章懂得任用买办与商业人士(例如盛宣怀)等来处理实业问题,既持官印,又打算盘,也就是找对的人做对的事。张之洞却是把炭火都往自己的头上堆!
张之洞在铁厂人员管理上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冗员”,也就是在同一部门中同一职位的人员过多。当初,这是张之洞为了实现各个职位之间的相互牵制而刻意为之的。以厂内文案为例,该职位日常工作仅为铁厂与外部的信件往来,一个人完成工作绝对绰绰有余,然而张之洞在设置该职位时便已编制为三人,只不过其中两人无须到岗,仅一人工作即可。但是在张之洞看来还是不够,居然其后又增加一人。1896年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发现仅马鞍山煤矿一处的同一工种同一职位的“主管”居然有30多人,由此可推断铁厂自成立时起,所养“闲人”就数以千计。这笔庞大的开销,对于本来就资金短缺、连年亏损的铁厂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张之洞采用如此浮夸的人事制度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需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人事请托,这让他不得不照单全收,从而迫使他的“中学西体”变了调[20]。总之,虽然张之洞草创了事业,但是没有专业队伍来一起奋斗,缺乏专业人士来干实事,最后能人也待不久,这事业也撑不久了。
追根究底,张之洞虽然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但是他只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其他方面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是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仪器炼出铁,建成铁路,用什么方法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选,那还是中国传统的衙门式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毕竟他还是得做官,必须处理好各方关系。近代西方企业使用所谓的“章程”或者“制度”管理企业,汉阳铁厂的管理则是“人治”。即使生产过程中出现相同问题,不同上级领导不免有着不同的处理办法,甚至同一个领导在不同时间也有着不同的处理办法。这种毫无章法、“拍脑门”式的企业管理模式,只能将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
管理企业与带兵打仗其实是一样的,“人治”相比于“制度”也许在短期内更加灵活,但是建立并遵守制度更能使企业永续发展。纵观古今中外,纪律严明的军队比较有机会在战场上获胜。《孙子兵法·始计篇》强调:“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规章制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在会计审计、金融管理、生产营运、人事制度、绩效考核、法规法务、战略规划等方面建立实际可行的规章制度。现代企业已经将自身的规章制度视为企业文化与运营的重要框架,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凝聚力的表现,那么规章制度就是强力胶,可以将企业中的每个人牢牢地粘在自己的职位上,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样才能使企业在稳定中向前发展。反之,缺少规章制度的企业就像是白蚁塔,从外面看巍然耸立、坚固无比,然而内部却有着千百个窟窿,经不起任何外部的冲击,甚至轻轻一碰便轰然倒塌。再者,衙门式管理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弊病——贪腐舞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当时老百姓对清朝政府部门最真实的写照。张之洞将衙门搬进了汉阳铁厂,便已经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可见革命也要革心,洋务运动既要引进西方的科技新知,也要学习其规章制度和企业精神。张之洞深谙官场经营与人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但却自始至终以抱残守缺的视角解读“中学为体”,在还未真正实现“西学为用”的理想抱负之前,反而先遭遇了铁厂的亏损。
更直白地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以及李鸿章的“全盘西化”,其实都是双方高喊的政治口号、在封闭的中国拳击舞台上寻求打击对方的手套,慈禧则是扮演裁判的角色。换言之,张之洞后来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慈禧的重视,离不开其制衡李鸿章的作用。虽说近代化势在必行,至于各自的理论依据或是实质内容则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认真了,那就很可能落入口水纷争的旋涡。实质上,清朝末年的近代化就是在看似“开明专制”的外表下,两派人马互相倾轧,并积极大搞试验求变的戏码,主政者则是高高在上调和二者。
(三)主事者事必躬亲,盲目自大
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生前理政可谓“上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从无宴乐事”,凡事勤勉克己,实属中国帝王中少见的特例。只是自嘉靖皇帝无为而治之后,明朝的国力便日渐衰弱,直至崇祯皇帝这一代,大明王朝可以说是由内而外全面溃烂,摇摇欲坠了。崇祯皇帝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个“烂摊子”,痛心疾首但是也充满干劲,他兀自认为只要自己事必躬亲,这个国家会慢慢恢复元气的。但是根本问题是:方法对了吗?
事后印证“事必躬亲”与“效率低下”并无不同。即使在最后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崇祯皇帝还要亲自处理紫禁城内太监与宫女“对食”这样的小事!这位瞎忙的皇帝,搞不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由于治理无方,只好利用“忙,盲,茫”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再者,“事必躬亲”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不懂装懂,胡乱指挥。说穿了,就是用独断专行来展现自己的权威,利用发号施令来刷存在感,因此最后的困窘结果并不难想象。
许多人批评张之洞对于汉阳铁厂的经营管理方法,与崇祯皇帝对于大明王朝的治理并无二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强行打开了国门,这样的开放确实是屈辱的,就在大部分国人还沉浸在悲痛与愤懑之中时,一部分目光敏锐、头脑冷静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但是他们并不自怨自艾,而是在满目凋敝的中国大地上看到了希望,张之洞便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模仿西方办工厂搞生产,就一定能够摆脱困境。带着对国家弱小的心痛与国家强盛的愿景,张之洞满怀热情地创办了汉阳铁厂,希望用中国制造的钢铁修建中国的铁路,这些人看到了西方的科技器具与成果,却忽视了对方软件工程的进步之处,不愿反思自己已经固化的思维逻辑是否曲解或是误解了中学与西学,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将中学与西学清晰地分割为“体”与“用”两部分,主观认定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做人皆学问,而做事只要有钱、有权就可以水到渠成。只是这样的思维实则是在抗拒思想与体制方面的改革,对于这样故步自封的行为,历史已经给予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很可惜,在清朝最后的岁月中,一些达官显贵也存有类似的看法,坚持“中学为体”成了政治表态的必要标志。
只是久居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越俎代庖、鸠占鹊巢的事情见得太多了,如果张之洞将铁厂的管理权下放,难保以后不会出现他不愿见到的局面。例如,北洋集团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插手铁厂事务,如果铁厂在经营管理上出现分歧甚至是内耗,若是不直接介入导正,不正给了北洋集团可乘之机?如此,恐将冲击到张之洞以及整个南洋集团。思虑再三之后,张之洞干脆将铁厂的经营管理之权全盘揽在自己手中。只是张之洞的专长全然不在经商营运方面,他对炼铁技术更是知之甚少,揽权之后的张之洞又如何能好好地经营管理铁厂呢?除了事必躬亲,确也别无他法了。我们得到的教训是:身为管理者之所以喜欢揽权,究其本质不外乎因为对自身能力的过高评估,对外部环境的过于乐观,或是拒绝竞争,干脆关起门来干的心态。喜欢揽权的管理者通常固执己见,并且周遭环境也不接受质疑的声音。各种问题在张之洞实际经营铁厂之后便一一显现出来了。
既然是在西方科技指导下办成的铁厂,那么技术问题最为关键。张之洞却从未熟悉炼铁的流程,在他看来用什么方法炼铁并不重要,他甚至兀自认为中国的炼铁术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只要能够使用西方机器即可大量炼铁。因此,当他购买英国炼铁设备,被英国公司要求先勘定煤铁矿源并检验矿石成分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并未与洋矿师白乃富沟通商议,而是一口回绝了该专业要求。最后的结果是,即使运用这批花高价从英国所购买的当时最先进的炼铁高炉,所产出的生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与预期的相差甚远。张之洞事后才派工程师与英国公司接洽,发现该炼炉适合用酸性工艺进行生铁冶炼。然而张之洞在当初下令生产时,使用的是距离汉阳50里远的江夏马鞍山矿源的白煤矿,该煤矿以及炼炉内部的耐火砖形成的是碱性炼铁条件。除了生产出来的成品生铁不尽如人意之外,在酸性炼铁炉使用碱性炼铁方法,也会大大缩短炼铁炉的使用寿命[21]。这一切的后果,都是由张之洞不懂技术却又盲目自大,不听从专业建议而直接造成的。
可见管理工作不只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篇》),更应该是要看重技术活、科学活的基本功,进而层层把关的品管过程。先把形而下的品管做好,再谈形而上的策略,所以说这是事业与艺术并重,不宜偏废,并且以看似小事的为先为要,诚如《圣经·路加福音》16∶10所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在企业财务方面,张之洞受到当时清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青睐,慈禧甚至愿意将其修整颐和园的部分款项拿出来支持张之洞办铁厂,这等于得到当时中央执政者的全额担保与支持。当时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清廷上下一心,拨款的请求自然不会被拒绝。况且两湖地区自古富庶,种种外部情况让张之洞自信满满,从建厂到投产几乎从未为资金发愁过。张之洞在建厂初期购买炼铁设备时并不是以炼铁需求、矿石适用要求或是企业预算为考虑因素,而是要体现“天朝之威”,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遇到质疑的声音,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张之洞既是铁厂的“总经理”又是湖广总督,有人戏称他的一声咳嗽就能够压盖住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只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一是因为当时整个清朝都处于财政疲软的状态,持续向铁厂拨款根本上是无法实现的;二是铁厂投产之后,产出与之前的预期相差甚远,非但没有任何盈利,反而每日亏损2000两白银。此时的张之洞并没有及时地找出病灶,而是“一刀切”地将紧缩政策作为铁厂救急的财政政策,他要求铁厂的任何开支都必须经由他的批准,大至设备的购买,小到一辆牛车的租用,唯有他点头许可才能办理。可惜的是,铁厂内并没有顺势颁布任何关于财务的规章制度,只是坚持但凡和钱有关的事项全部由张之洞一人决定。《钟天纬致盛宣怀函》中批评当时的张之洞:“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权,总办不能专主,委员更无丝毫之权。用款至百缗(1缗等于1000文铜钱,约合人民币140元)以上,即须请示而行。”
“清流派”书生往往重理学,好空谈,轻实术。不擅长商务亦不擅长企业管理的张之洞确实无法带领铁厂继续向前,更可惜的是他不愿找人或是找不到对的人来管理。一个企业在生产之前,都会对原材料成本以及产品销路进行充分的评估,即使张之洞这种“清流派”的领袖,也在建厂之前做了这些评估,只不过所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想当然,前期的调研不深入、力度不够,最后肯定会在市场上吃大亏。建厂之前,张之洞最终以“煤铁两就”为理由选定汉阳,又认为铁厂地处武汉这一长江流域的交通要道,更有卢汉铁路修建,铁厂产品何愁卖不出去等预期,而过分乐观地评估了当时的钢铁市场。真正开工投产后,由于炼铁的煤矿不符合设备的酸碱环境要求,汉阳铁厂不得不放弃马鞍山煤矿而改用山西、内蒙古一带出产的焦炭,这样一来使得生产成本瞬间翻了好几番。不过,要是出厂的产品物美质优,那么在销售环节的盈利或许可以弥补成本所带来的损失。然而,由于炼铁技术不成熟,加之企业管理混乱难以留住专业的炼铁人才,即使之后在炼铁工艺上进行了改进,汉阳铁厂生产的钢铁产品最终还是存在浓度过高的杂质,无法与洋铁在质量上竞争。而且采购炼铁设备、远途运输煤矿而产生的高额成本,导致售价居高不下。这样一来,不仅国外不愿意采购,就连国内的厂矿企业也是兴趣不大。为了救活铁厂,张之洞想尽了办法。他曾经规划将官办企业、事业企业作为铁厂的主要销货对象,并且拟定了一系列的价格优惠方案和服务细则,其中就有“所有北洋铁路局及各省制造机器、轮船等局需用各种钢铁物料,或开明尺寸,或绘寄图样,汉阳铁厂均可照式制造”。不论如何,张之洞仍然不顾或是无法看到汉阳铁厂自身的经营弊病和所产钢铁产品的品质漏洞,他一直把汉阳铁厂的不利局面归咎于国人不能同心支持汉阳铁厂的发展。他在1896年6月26日的《张之洞奏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中抱怨:“中国苦心孤诣,炼成钢铁,不异洋产。万一各省办事人员,以意见为好恶,仍舍其自有而求诸外人,则自强之本意既大相剌谬,厂商之力量亦必不能支。”从张之洞的这些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与痛心,同时对他的自负感到唏嘘。
如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样,人欲尽其能,必先找对位。用人的艺术首要在于识人知人,然后才有可能知人善任,让对的人在对的岗位上做对的事。这些基本条件缺一不可,不宜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