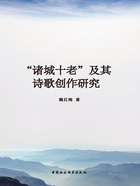
三 明末清初的诸城形势
如果说“诸城十老”面临的社会大环境是当时汉族读书人所共同面临的处境,而山东又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扮演了较早归顺的角色,那么,在诸城境内遭遇战乱袭击的“诸城十老”,又该何去何从呢?
诸城在明朝年间遭遇的战事极少,基本上是太平无事。“时四方无事,夜不闭户,常于三更夜读后,月上雪晴,游于峰顶,燎薪达旦,乐而忘曙”[26],即是当时诸城读书人生活常态的写照。
然自崇祯四年(1631)年末,诸城周边不时传来兵乱的消息,并最终殃及诸城。
崇祯四年十一月,明朝武将孔有德率兵扰乱山东,先后攻陷了陵县、临邑、商河、新城等地,长驱进入胶东半岛。次年正月,他率兵攻下登州、围攻莱州,与城内明军形成对峙,搞得人心惶惶,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在明朝大兵的攻击下,于崇祯六年二月撤离山东。
崇祯十二年,清军侵占济南,战火虽未波及诸城,但丁耀亢等人却已经感觉到了“世变人情将入劫,道穷吾党各争机”[27]的战争预兆。
崇祯十五年,清军再一次大举侵犯山东,战火蔓延至诸城,诸城遭遇重创。这次战乱,不仅县志有记载,还被记录在时人诸多文集中。虽然乾隆《诸城县志·总纪上》只是简单地记载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我大清兵略地至县,城破”;“十六年春三月……我大清兵北归”[28]。但一个“城破”,足以说明此次战乱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惨状。其余行文里,亦不时流露出战乱给诸城民众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在经历过战乱的人物传记之中:
卷三十三《李卜之传》:“崇祯十五年之变,甫七岁,为大兵所获,日夜泣呼父母,哀恸行间,主将怜而归之。”
卷三十三《刘果传》:“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土贼多乘机劫掠。”
卷三十四《李佐圣传》:“(崇祯)十五年冬,大兵东下,佐圣兄及弟皆被杀。”
卷三十四《台瞻斗传》:“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瞻斗为铁骑所得,携至沈阳编隶,日负水,久之作苦。”
卷三十四《杨蕃传》:“崇祯十五年,城破,良家子争逃窜,宗儒为饘粥给资斧,全活甚众。”
卷三十八《王之塇传》:“崇祯十五年,城破,死之。”
卷四十一《王溥传》:“崇祯十五年,大兵过相州村,杀数百人。”
除了县志,当时还有很多人在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战乱所带来的灾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诸城十老”。时年四十四岁的丁耀亢对这场战乱的体验最为深刻,其杂著《出劫纪略》就多次记载这次战乱,尤以《航海出劫始末》一文的记录最为详细:崇祯十五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清兵攻陷了诸城,“是夜,大雨雪,遥望百里,火光不绝。各村焚屠殆遍。明日,得破城之信。遣役往探,东兵已据城”。此时的诸城,到处是破败荒凉的景象,满眼是“白骨成堆,城堞夷毁,路无行人。至城中,见一二老寡妪出于灰烬中,母兄寥寥,对泣而已”;社会秩序更是混乱,“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城中仕宦屠毁尽矣”。[29]李澄中《与李辉岩使君》则曰:“诸自壬午罹兵燹,继以戊申地震,当时抚君刘增美先生勘荒,谓东省被灾之惨,惟诸为甚。”[30]张侗《卞氏传》也有描述:“壬午后,海上大乱,壮者毙锋镝,髦稚累累填于壑。”[31]
诸城兵燹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灾难,身处其境的“诸城十老”亦深受其害。其中丁耀亢、张衍和张侗、隋平等家族损失尤为惨重,不仅财产丧失大半,还失去了许多家族成员。
诸城战乱时,丁耀亢虽然带领老母亲、妻儿等逃到了海州清风岛避难,但他的大哥丁耀斗、胞弟丁耀心和侄子丁豸佳、丁大谷等人,却因率领民众护城而伤亡惨重,“胞弟举人耀心、侄举人大谷皆殉难,长兄虹野(丁耀斗)父子皆被创,居宅焚毁,赤贫徒步,奴仆死散殆尽,苟活而已”[32]。对此乾隆《诸城县志》亦有记载,如:
卷三十一《丁 传》:“崇祯十五年,父大谷遇害,
传》:“崇祯十五年,父大谷遇害, 年十四,忍泣不敢哭。藁葬后,乃与族兄亮共舁祖母逃入山,备极艰苦。”
年十四,忍泣不敢哭。藁葬后,乃与族兄亮共舁祖母逃入山,备极艰苦。”
卷三十六《丁豸佳传》:“崇祯十五年,为大兵所伤,跛一足,遂无意进取。”
卷三十八《丁大谷传》:“十五年之变,大谷出赀纠乡兵防守。城将溃,遣其子 归侍老母,曰:‘吾不返矣。’遂死于东门。后志载守城殉难者,又有丁耀心、陈司铎、鉴桂三人,皆举人。”
归侍老母,曰:‘吾不返矣。’遂死于东门。后志载守城殉难者,又有丁耀心、陈司铎、鉴桂三人,皆举人。”
卷四十五《列女传》:“聂氏,举人丁大谷妻。崇祯十五年城陷,大谷遇害。聂曰:‘良人世族,死而无传,吾不忍也。’指幼子 曰:‘存尔父者,惟吾与汝。’遂携
曰:‘存尔父者,惟吾与汝。’遂携 以逃。兵退,收大谷尸葬之。”
以逃。兵退,收大谷尸葬之。”
时隔多年,丁耀亢对诸城战乱带来的伤痛仍难以忘怀,在他的诗文中还是一再提及:“避兵入海,城廓非故。家无遗粟,人如脱兔”(《自述年谱以代挽歌》),“謇壬午之遘祸兮,城邑沸而土崩”(《怀仙感遇赋》)。晚年,看着死于战乱的二哥丁耀昴遗留的故居,依然发出“乱后池塘已半非,孤坟松柏尚依依”的感慨,一想到二哥之子丁延绪“身后遗孤遇乱无”(《丁未人日过亡兄觐微旧居有感二首》),就很伤感。
同样的,张衍和张佳之生母徐氏在战乱中的罹难,亦成为张氏族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痛与恨。对徐氏遇难一事,李澄中在《张母徐孺人墓表》有详细记载:“明壬午岁,清兵下山左,诸郡县多残破。其明年正月二十六日,铁骑大至,孺人从邻妪匿场圃积草中,为兵所获,刃数人,孺人绐之曰:‘予汝金可免死否?’兵喜随至门,孺人自计曰:‘此吾死所也。’反骂兵,兵怒,抽矢射之,遂死。”[33]张母徐氏如此悲壮的惨死,成为张衍和张佳一生的痛。张衍“暨母氏徐孺人死于兵难,哭祭终身”[34];张佳在徐母殉难时只有五岁,成年后“塾师命题今之孝者,佳属草泪下,卷尽湿”[35]。
隋平的祖母王氏,亦在这场战乱中遇难。乾隆《诸城县志·列女传》记载:“王氏,诸生隋毓仑妻,年二十一。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王时已寡,匿穴中,铁骑搜得之,置马上,王自投而下,以首触刀环,不屈,死。”[36]
战乱发生时,十四岁的李澄中随父亲李凤郊和二哥李述中(字彭仲)逃难,成年之后对这场战乱依然记忆犹新。其《先仲兄彭仲公行状》一文云:“壬午岁,值兵乱,杀人遍原野。当是时,兄年十八,予甫十四。先府君携两幼子出入兵火间,日夜忧思,无所赖。兄乃为孺子戏以娱先府君意,又识趋避以左右先府君,故卒免于难。”[37]虽然李澄中家族在战乱中没有人员伤亡,但他日后回忆起经历过的战乱仍是厌倦的,“四海有秋今细雨,十年无事厌谈兵”(《雨后喜徐栩野至自渠丘》),“地僻闻豺虎,身衰畏鼓鼙”(《端阳后二日与赵壶石过放鹤园纪事》)。
可以说,这场战乱让许多诸城民众家破人亡,带来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明清鼎革。丁耀亢《山居志》亦云:“是年冬,乃有屠城之变。山林化为盗薮,浮海余生,流离南北,藏书散失,云封苔卧,而主人为逋客矣。”[38]
然城破后,诸城民众还没来得及修复伤痛的心情,各类“土寇”、“土贼”层出不穷,“甲申春,土寇复炽”、“至三月闻闯信……(三月终)乃知有闯逆之变”[39],“顺治元年,土贼丘凝休、王玉山等聚众攻城”[40],“顺治元年,土寇李德斋等掠其村,祖通死之,桢右背被伤”[41]。直到顺治七年,“土贼”依然不时地引发骚乱。他们的出现,无疑更加剧了诸城民众的苦难,“时残破之余,劫杀相习。乱民经闯宦纵恶之势,藏身衙胥,以巨室寒士为奇货,草野之间,动相杀害”[42]。仅乾隆《诸城县志·列女传》中,就记载了诸多因这一时期迭起的战乱而丧失性命的女性:
“郑氏,员外郎刘必显妻,事舅姑,至孝。崇祯十五年,大兵东下,土寇乘间窃发,举家避难胶州孝苑村。寇围其屋,郑矢死不辱,自缢死。”
“郑氏,生员王沛恺妻。崇祯十五年从姑曹避乱琅邪台,寇欲辱之,骂求死,妇姑乃同毙于台下。”
“马氏,逸其夫名。顺治元年,土寇至,夫与子皆被杀,复系马将出门,马绐之曰:‘吾家井中有财物,可返取。’比至,投井而死。”
“沈氏,孝子王斗维妻,年二十三。值土寇蜂起,斗维以庐墓被杀,沈哭曰:‘子从父死,妻不当从夫亡乎?’戚党劝之乃止。抚周岁孤儿伟,备尝艰苦,躬亲教诲。至顺治九年,西山土寇至,或劝之避。沈曰:‘夫柩未葬,去将焉往,此吾从夫地下时也。’寇至大骂,遂于斗维柩前遇害。”
以上仅仅是死于战乱的有名可考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是籍籍无名的普通民众。据康熙《诸城县志·户口》记载:直至清朝定鼎,诸城人口从四万六千多减至不足一万。[43]
因为战乱迭起,诸城不仅有许多民众失去了生命,还有大批民众的财物被掠夺。如乾隆《诸城县志·列女传》记载:“崇祯十五年,(李)作哲死于兵,作圣、作谋被掠,李氏无孑遗,田园为豪强夺去。”
这种惨痛的经历,丁耀亢都有切身体验,其《保全残业示后人存记》就有详细记录:“至甲申入海,而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鼎沸,大家茫无恒业。”[44]
从以上叙述中可知,乾隆《诸城县志》所言“城破”,也暗含着另一层深意,即诸城士绅率领民众誓死抵抗清军入侵,护城卫家,直至城破殉国。
除了丁耀亢家族成员参与护城外,与“诸城十老”交好的臧氏家族也参与了守城,并且是人员伤亡最惨烈的家族,乾隆《诸城县志》对此亦有记录:
卷三十一《臧允德传》:“崇祯十五年,家门多死难者,允德于兵燹中,厝置数丧,皆尽礼。”
卷三十八《臧尔令传》:“崇祯十五年冬,大兵南下,缙绅分任守城之责,尔令率子姓守西南隅。十二月十四日,城破,遇杀。……(子)世德已脱于难,闻父变,奔至,抱尸大哭,遂遇害。永德以力战,死于西南门外。尔令弟尔寿、兄子嗣德,俱同日死。”
卷三十八《臧尔寿传》:“城破,(臧尔寿)死。”
卷三十八《臧嗣德传》:“大兵入,(臧嗣德)衣朝服,端坐厅事,遇害。”
因此可以说,自诸城战乱始,诸城民众就陷入了无法阻挡的灾难里,处于社会动荡的水深火热中。清兵入侵造成的破败和社会混乱还没有结束,各路“土贼”、“土寇”的骚扰又不断兴起,“何处求安土,残城又负戈”,再加上官府的催科,“官兵犹报捷,县令正催科”(《闻辛卯三月贼过诸城》)[45],还有旱灾、蝗灾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不断侵袭,种种灾难叠加在一起,将诸城民众推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可以说,早在明清鼎革、山东投降的局势出现之前,崇祯十五年的清兵入侵诸城,已经给了诸城民众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这种打击带来的伤痛不是一人一时的,而是诸城民众几代人共同的伤痛。所以当李自成义军入侵诸城、诸城境内及周边“土寇”频起以及明亡清立的消息接踵而来,这对诸城民众而言,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伤口撒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