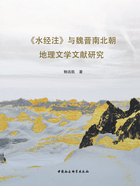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的人物故事叙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人物传记的撰述开始走向繁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所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60],即是当时传记著作繁荣的真实记述。当时的郡书和地记,记载了众多的地方人物故事。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把郡书和地记(地理书)归为杂述(即杂传)一类,认为其亦能在正史以外“自成一家”且“能与正史参行”。确实,郡书和地记通过记述地方耆旧、先贤、名士等的故事言行,存录了当地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具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价值,也有较大的文学价值,值得加以认真研究。
一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撰著繁荣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书渐趋兴盛发达。《隋书·经籍志》著录“杂传”139部,其中属于地方人物传记的,就有《益部耆旧传》(陈长寿撰)、《汝南先贤传》(魏周斐撰)、《陈留耆旧传》(魏苏林撰)、《陈留志》(东晋江敞撰)、《襄阳耆旧记》(习凿齿撰)、《会稽典录》(虞豫撰)、《豫章烈士传》(徐整撰)、《豫章旧志》(晋熊默撰)、《零陵先贤传》《桂阳先贤画赞》(吴张胜撰)、《长沙耆旧传赞》(晋刘彧撰)等,共32部。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杂传类著录有圈称《陈留风俗传》 (不同于《陈留耆旧传》)[61];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又补录《荆州先贤传》 (晋高范撰)、《广陵烈士传》 (晋华鬲撰)、《广州先贤传》(刘芳撰)等9部[62];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又补录《山阳先贤传》(周斐撰)等4部[63];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又补录《广陵耆老传》《贺氏会稽先贤像赞》2部[64];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又补录《续益部耆旧传》(常宽撰)1部[65]。从以上著录情况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人物传记50部左右,还不算许多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传于后世的著作。这足以说明当时地方人物传记撰著之繁盛。所以,有学者指出:“不论在著作的数量,或对于杂传形成的概念方面,都显示出杂传是魏晋时代新兴而又非常流行的历史著作形式。”[66]同时,记人系列的地记,也与当时地方人物传记繁盛的情况成正比。很多地记,如晏谟《齐地记》、环济《吴记》、佚名《江东旧事》、裴渊《广州记》、陆翙《邺中记》、江敞《陈留志》、习凿齿《襄阳记》、史筌《武昌记》、张僧监《寻阳记》、刘道真《钱唐记》、盛弘之《荆州记》、沈怀远《南越志》等,也都记有不少地方人物事迹。
地方人物传记何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繁盛?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政治制度、时代思想的影响,以及史学发展的内在需求都有一定关系。
(一)地方宗族势力的壮大
自两汉开始,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豪强地主崛起。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国立基,也曾借助于豪强地主集团的势力,于是东汉豪强地主得以参与政治。刘秀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刘秀所说的“柔道”,就是对豪强地主宽怀纵容、扶植保护。
于是,豪强地主拥有了大量的土地以及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有了经济方面的保障后,一些豪强地主致力经学,形成自家家学,为日后士族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豪强地主集团还假借察举制操纵选举,推举本族士人,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而本族士人致仕返乡,即成为地方宗族大姓,在朝野均具有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东汉后期,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又得到发展抬头的机会,各州牧拥兵自重,各霸一方。这样群雄割据的局面,对士人的政治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地域性的乡土情怀逐渐取代了大一统情怀。这是地方人物传记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晋之际,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侨土”地方界域使得南渡世族的宗族意识和乡园意识更加浓厚,常常思追故里。新亭对泣时周顗“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即为例证。另一方面,南方的大族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也日益注重文化底蕴的发掘。于是,世家大族为了在地位争夺中取得一席之地,纷纷撰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67]。地方人物传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得以持续繁荣。
(二)地域文化与乡邦意识
袁宏《后汉纪》卷九云:“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禀,生其山川,习其土风。山川不同则刚柔异气,土风乖则楚夏殊音。是以五方之民,厥性不均,阻险平易,其俗亦异。”[68]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生长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们,在文化、风俗、亲情等方面,会自然形成一种心理认同,即通常意义上的“乡邦意识”。这种“乡邦意识”是人与地的一种自然情感,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
有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州郡地记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后认为:“魏晋南北朝地记以州郡记为最多,而州郡记中近半者,是作者记载自己的家乡,且作者多为文化士族;这种状况既是当时门阀士族重郡望的表现之一,也是本土地域意识发展的结果。……各地都有其地域性,或起因于自然条件,或因历史传统、社会条件而产生,亦源于其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者。魏晋南北朝各地地记发展的不平衡,既反映了诸州地位与传统的不同,也反映出各地士人地位和心态的差别。”[69]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常璩《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记载了蜀人常宽因为蜀中叛乱流离到交州时,撰著《蜀志》的情况:“虽流离交域,衣敝缊袍,冠皮冠,乘牛往来,独鸠合经籍,研精著述。依孟阳宗庐师矩著《典言》五篇,撰《蜀后志》及《后贤传》。”[70]常宽是蜀郡江原人,在流离异域、生活贫苦的情况下,仍能致力于对本土人物传记的撰著,足见其乡邦意识浓厚。常宽是常璩族祖,据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常宽还撰著有《续益部耆旧传》二卷,前文已列。
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说:“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71]魏晋南北朝郡书和地记,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郡书和地记的作者,很多都是本土作家,出于对乡邦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熟悉与自豪,所以在著述中表现出了浓郁的乡土意识,极力夸耀家乡地理之美、物产之丰、人物之盛。
(三)选官制度和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
东汉选官制度采用荐举制,但实际上选举系于阀阅渐成为社会风气,大姓冠族往往操纵选举。汉末,选举制度以名士清议为基础,因而名士清议就显示出其重要作用,由此促成了人物品评之风气。正如汤用彤指出:“溯自汉代取士大夫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为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士风亦竞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迸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72]为求仕途进取,地方大族纷纷相互交结,博取盛名。于是门阀势力的文化标榜,成为其时的社会思潮。郡书渐盛,与此相关。
魏晋以后,采用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官:“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73]但这实际上加强了士族权力,因为担任各级中正官的依然是世家大族:“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世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门第和家族背景依然是选举的重要参照。为显示自身在文化上的优势,各地方大族特别关注本乡本族人才,并由此促进了郡书等地方人物传记撰著的兴盛。逯耀东认为:“由于东汉帝国崩溃后,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因而使原有地域性变得格外尖锐化。魏晋士人阶层中各言其地风土之美、人物之俊,彼此往复论难以此为据。因此,形成魏晋杂传中以地区为主体的先贤、耆旧等类传。”[74]实如其言。
(四)史学的发展的需要
有学者说:“记人系列的地记,较多的具有历史学的性质,它们的崛起,和晋宋史学的兴盛息息相关。它们的大量涌现为地记之作的繁荣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75]地记与郡书等地方人物传记,与当时史学的兴盛确实存在这种互动关系。
汉末以来,经学的衰落,正好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史学逐渐被人们重视。史学教化功能的凸显、史官的建置,都推动了人物传记撰写。清代学者章学诚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76]按章学诚的说法,地方人物传记撰著的盛行,应有补充正史撰著不足的功用。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郡书等地方人物传记经常出现于史书的注文,有些正史未为……立传的人物事迹也可得之于郡书,还有些史书内容直接取材于郡书,如《后汉书》中有些人物传记内容,与陈寿《益部耆旧传》所记内容基本一致,而众所周知,《益部耆旧传》成书于《后汉书》之前。
二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的人物故事类型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说:“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77]章学诚从史学家的角度,按照修史原则的要求,对魏晋以来包括地记郡书等在内的杂传进行了批评。然而,正是由于杂传作家在作品里的这种自由表达思想的“滥漫”,文学色彩才逐渐转浓。魏晋南北朝记人系列的郡书地记,很多已经离史独立,成为独立的写人的文学,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表现出浓重的文学意味。就其情节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颂扬官员惠政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中记载了一些官员的从政业绩。
写官员仁爱百姓的如吴张胜《桂阳先贤画赞》:“临武张熹,字季智,为平典令。时天下大旱,熹躬祷雩,未获嘉应,熹乃积柴自焚。主簿侯崇、小吏张化,从熹焚焉。俟火既燎,天灵感应即澍雨。”[78]张熹是一位仁爱百姓的官员,其舍身为民祈雨的献身精神,未必能打动上天,却明显得到了百姓的褒奖和称赞。
写官员廉洁奉公的如《陈留耆旧传》载:“洛阳令董宣死,诏使视之,有简典一乘、白马一匹。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79]这位洛阳令董宣没世后家无余财,足见其清贫廉洁。
写官员教化民风的如《汝南先贤传》曰:“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於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80]此节突出了周举的劝民教化之功,后来南朝宋范晔将其全文录入《后汉书·周举传》,仅仅改动了几个字而已。《零陵先贤传》曰:“郑产,字景载,泉陵人也,为白土啬夫。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产乃敕民勿得杀子,口钱当自代出。产言其郡、县,为表上言,钱得除,更名白土为更生乡也。”[81]郑产本非高官,仅是个乡长的角色,但他心存仁义,不但劝导百姓,还勇于为民请命,受到百姓的尊敬,改乡名为更生,以彰其再生之恩。
写官员严明执法的如《长沙耆旧传》记载虞芝严明执法,不畏权豪的事迹:“虞芝,州命部南阳从事。太守张忠连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执案,刺史畏势,召芝。芝曰:年往志尽,譬如八百钱马,死生同价。且欲立效于明时耳。遂投传去。”[82]虞芝奉公守法,不畏权贵,敢于规矩上司,甚至顶着生命冒险惩办不法王亲,是一位执法如山的官吏。
(二)彰显乡贤德行
“乡贤”是本乡本土的才德之士,因德行、才能、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所尊重。其耆老望重者,有敦孝悌、笃宗族、维持风化之责。这些乡贤的嘉言善行,被郡书地记作家记载下来,其中不无感劝闾阎、教育后辈、揄扬本乡民风的用意。
《汝南先贤传》曰:“阚敞,字子张,平舆人,仕郡为五官掾。时太守第五常被征,临发仓卒,有俸钱百三十万,留付敞。敞埋著堂上,遂遭世仓卒,道路断绝,敞年老饥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钱,可取自给,然后偿之。敞曰:吾穷老,何当有用故君之财耶?道通当送,饥寒何损。常举门遭疫,妻子皆死。常病临困,唯有孤孙年九岁,常谓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舆阚敞钱三十万。气遂绝。后,孙年长大,步担至汝南问敞。敞见之,悲喜与共临发阱钱,乃百三十万。孤孙曰:亡祖临终言有三十万耳,今乃百三十万,不敢当也。敞曰:府君病困,气索言谬,误耳。郎无疑也。”[83]阚敞诚实守信,虽然贫困偃蹇,对故人所托之物也绝不染指,并断然拒绝妻子的建议,当故友后人来寻后,如数奉还,显示了其清廉自守的品德。
《益部耆旧传》载:“赵典为太常,虽身处上卿,而布被瓦器。”[84]又载:“阎宪为绵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于路,得遗装。开视,有锦二十疋,明早送诣吏曰:县有明府君,犯此则惭。”[85]赵典贵为上卿,而“布被瓦器”,清廉之行,堪为表率。而第二则写平民杜成的拾金不昧而顺及县令,实写上行下效的政治效果。
又如晋张方《楚国先贤传》:“(韩)暨临终遗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代送终过制,失之甚矣。若尔曹敬听吾言,敛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86]韩暨以俭朴为德,遗言薄葬,显示了他恭谨守礼的品格。
《寻阳记》还记有董奉济世救人的故事,说的是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得愈者令种杏五株:“杏在北岭上,有树百株,今犹称董先生杏株。”[87]现在“杏林”已经成为中医学界的代称,人们往往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
(三)表彰节义之士
郡书地记作家一般以儒家观念为基础,对地方贤德人物的品行进行记述。所以在作品中记载了一些当地的忠义之士。如《益部耆旧传》:“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县主簿。县长广都朱淑以官谷割免,当论重罪。播争狱讼,身受杖数千,披肌割肤,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每将掠拷,吏先验问伏不,播答言:愿得罚,无所多问。辞终不挠,事遂见明也。”[88]常播的上级朱淑因为割免官谷救济百姓而被论以重罪,常播勇敢地站出来解释,虽然“身受杖数千,披肌割肤,更历三狱”而不改口,是一位义字当先的硬汉。类似的事情,《桂阳先贤画赞》也有记述:“耒阳罗陵,字遂文,果而好义,郡长汲府君为州所诬,罗陵被掠考,参加五毒,陵乃截舌以着盘中献之。廷尉群公咸共义之,事得清理。”[89]再如《广陵烈士传》记载刘儁“为郡主簿,郡将为贼所得,知言辞不能动贼,因叩头流血,取而代之。贼不听,前砍府君。儁因投身,投之正与刃会,砍儁左肩,疮尺余。贼又欲更下刃,儁号呼抱持不置,贼因相谓曰:此义士,杀之不祥。遂俱纵遣”[90]。常播、罗陵、刘儁诸人,忠义可嘉,事迹感人。《汝南先贤传》载:“胡定,字元安,颍川人,至行绝人。在丧,雉兔游其庭,雪覆其室。县令遣户曹椽排闼问定。定已绝谷,妻子皆卧在床。令遣以干粮就遗之,定乃受半。”[91]故事中的胡定是一个耻于干谒、宁可饿死也不屈志的硬汉形象。
(四)宣传孝悌观念
为子当孝,为弟当悌。孝悌观念是封建社会的伦理常规。因此,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中记载了不少孝悌故事。如魏苏林《陈留耆旧传》:“后汉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旦,容杀鸡为馔。林宗初以为己设,既而容独以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劝之就学,竟以成德。”[92]又如《楚国先贤传》写孝子孟宗:“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如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累迁光禄勋,遂至公矣。”[93]又如《汝南先贤传》:“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环冢泣曰:顺在此。”[94]
郡书地记还记载有一些孝女故事。虞豫《会稽典录》载:“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为之作碑。”[95]《益部耆旧传》所载孝女叔光雄的故事,情节与此相类。
还有一些亲族兄弟友爱的事迹,也被记之于郡书地记。如《陈留志》:“李铨,字玄机,平丘人也。少聪惠,有志行。铨兄,前母子,后母甚不爱也,而衣食皆使下铨。始年五岁,觉己衣胜兄,即脱不著,须兄得与己同,然后受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长,铨内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闺门雍睦,为邦族所称。”[96]又如陈寿《益部耆旧传》:“李孟元修《易》《论语》,大义略举,质性恭顺。与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园,悉以让就。夫妇纺绩,以自供给。”[97]李铨友敬同父异母之兄,李孟元资助有疾病的堂兄,悌道可嘉。
(五)赞赏学识才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衰微,人们逐渐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使人们个人意识开始觉醒,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自身,乐于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此时的郡书地记记载了较多博学多才的乡邦人物,对他们的才智给予充分的肯定。例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98]写出了董扶的博学多识。又如,《武陵先贤传》曰:“潘京世长为郡主簿,太守赵伟甚器之,问京:贵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破。光武时移抬东山之上,遂尔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99]据《晋书·潘京传》:“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太守询问,潘京对答如流,从回答可以看出他的博学以及对乡土历史、地理的熟悉程度。
李泽厚《美的历程》说:“六朝时期,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准则。并不都是赫赫战功或烈烈节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操的精神、脱俗的言行。”[100]郡书地记还记载一些灵活机智的人物。例如,《长沙耆旧传》:“夏隆仕郡时,潘浚为南征太守,郡遣隆修书致礼。浚飞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于岸边拔刀大呼,指浚为贼,因此被收。浚奇其以权变,自通解缚,赐以酒食。”[101]夏隆随机应变,思超常人,以奇谋追上南征太守潘浚,完成了郡里的差事。再如,《会稽典录》载:“(孙)策功曹魏腾,以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追释腾。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102]孙策夫人凭借自己的智勇,力劝孙策,灵活机智地救下了将罹刀斧之刑的忠臣魏腾。
一些在某些方面有专长和能力的人物事迹,也被郡书地记记载下来。如《益部耆旧传》写一心算高手:“何祗补成都令,使人投算,只听其读而心计,不差升合,其精如此。”[103]再如元陶宗仪《说郛》卷五十八所辑《零陵先贤传》叙叶谭事:“叶谭,字令思,零陵人。少负节操,未几,举孝廉。王济谓谭曰:君,吴楚人也,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谭曰:君不闻明珠大贝独生江海之滨乎?武子为之默然。”叶谭言辞应对,从容不迫,才思敏捷,不卑不亢。
(六)反映社会风尚
魏晋时期人物品评风气兴盛,受其影响,郡书地记中有些作品着重于书写人物容貌、神态、才情等,并且更加注重体现人物外形下所显示的内在精神。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周斐的《汝南先贤传》。《汝南先贤传》对人物的品评与赏鉴,既体现了时人清议的风气,又对近两百年以后问世的《世说新语》的写法开启了法门。如:“谢甄,禀气聪爽,明识达理。见许子将兄弟弱冠之岁,曰:平與之渊有二龙出焉:察其盼昩则赏其心,睹其顾步则知其道。”[104]又如:“黄宪,字叔度,不矜名以诡时,不抗行以矫俗;窥其门者莫敢践其庭,睹其流者不能测其深。时人论曰:颜子复生乎?”[105]比较《世说新语·品藻》,不难发现二书彼此间的渊源联系。
魏晋士人具有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意识相当强烈,表明了人的觉醒。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也记述了较多在言行举止、节操风度、思想学养等方面特立独行的名士。如《汝南先贤传》袁安困雪一节:“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106]袁安困雪,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典故了。高士生活虽然清贫,但有操守,每令后人钦慕。后来人们经常把宁可困寒而死也不愿乞求他人的有气节的文人比作袁安。又如《陈留风俗传》:“阮简为开封令,时外白有劫,贼甚急。简方围棋,长啸曰:局上劫亦急。”[107]阮简遇急不慌,镇定从容,神态气量,跃然纸上。再如《襄阳记》记述庞德事:“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马德操尝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德公谈。其妻子皆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108]这则小故事记述了隐居高士庞德与诸葛亮、司马徽、徐庶等汉末名人的交往情况,显现了他们彼此间的融洽而默契的关系,状写生动。这些名士异行故事,隐含着打破偶像崇拜、高扬个体人格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文心雕龙·史传》说:“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但如果换个角度看,正是有了这些“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穿凿傍说”,才使得杂传增加了文采和趣味。何况便纵是对正史而言,“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思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109]
三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人物故事的文学性表现
朱东润说:“中国的传叙文学唯有汉魏六朝写得最好,忽略了这个阶段,对于全部传叙文学,更加不易理解。”[110]朱东润所说的传叙文学,便是包括郡书地记中的人物传记在内的各种杂传。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记载了许多人物故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貌,刻画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蕴藏着的小说情趣,体现了较强的文学性。
(一)人物形象的刻画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除了描写人物的行动、语言、心理、神情等外,有时还通过间接描写或对比衬托的方法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点。
1.行动描写。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常常通过描写人物富有特征性的动作,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如《楚国先贤传》:“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敬礼之。”[111]曹操主动交好宗承,但宗承并不妄与人交,搞得曹操很难堪。“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的动作,刻画出了宗承的耿直性格。后来曹操显贵,以为可以势屈之,但宗承依然傲岸如故。再如《汝南先贤传》:“许嘉给县功曹。仪,小吏当持剑侍及功曹,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嘉于是忿然叹曰:男儿为吏,不免贱役!投其炬于地,以剑带槐树,趋谒府门。”[112]“投其炬于地,以剑带槐树”的动作和愤激的话语,活画出许嘉的这个少年气盛、抱负远大的年轻人的形象。
2.语言描写。郡书地记中的人物语言,已经具有个性化特点,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汝南先贤传》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值汉桓之末,阉竖用事,外戚豪横,乃拜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害。”[113]“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言之铮铮,掷地有声,一个有志拯世救国的少年英雄形象,呼之欲出。又如盛弘之《荆州记》:“竹山县有白马塞,孟达为新城太守,登白马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不能守,岂丈夫哉!”[114]孟达之叹,尽显其横刀立马的英雄本色。再如环济《吴记》:“孙权诏曰:吕岱、诸葛恪《道步骘》说: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读此表,令人连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来,宁有可塞者乎?”[115]孙权听闻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不禁哑然失笑。言语情态,绘声绘色,在写法上具有情景化的特点,加强了记述的表现力。环济《吴记》还记载了吴主孙晧与张尚的对话:“晧尝问:《诗》云泛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对曰:《诗》言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也。又问:鸟之大者惟鹤,小者惟雀乎?尚对曰:大者有秃鹙,小者有鹪鹩。晧性忌胜已,而尚谈论,每出其表,积以致恨。后问:孤饮酒以方谁?尚对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发怒收尚。尚书岑昬率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116]在这个片段中,有孙晧与张尚的三问三答。不但引诗据经,更在简短的记述中写出了两个人的性格。孙晧买弄浅学,生性猜忌;张尚则倔强梗直,不稍迂回。
3.间接描写。郡书地记中在进行人物刻画时,有时恰当地借助一些侧面描写,就是通过引述其他人物对所写人物的感受和印象,来映衬、烘托出所写人物的主要特点。如《襄阳耆旧记》曰:“庞德公子奂,字世文。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去官归乡里,居荆南白沙乡。里人宗敬之,相语曰:我家池中龙种来里中化其德,少壮皆代老者担。”[117]庞奂去官归乡,必然以善言嘉行影响宗族乡人,所以才会有“少壮皆代老者担”的民风转变。但庞奂如何感染教化乡民,文中没有直接写,而是通过乡民的评价显现出来,这样就显得更为真实可靠。
还可以《零陵先贤传》为例。《零陵先贤传》有几处写周不疑:“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始婴孩时,已有奇异。至年十三,曹公闻之,欲拜识。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时有白雀瑞,儒林并以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异而奇之。”[118]“曹操攻柳城不下,图书形势问计策,周不疑进十策,攻城即下也。”[119]“太祖爱子仓舒,夙有才智,谓可与不疑为俦。及仓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谏以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乃遣刺客杀之。”[120]周不疑是与曹冲(字仓舒)相伯仲的神童,十七岁时被曹操暗杀。《零陵先贤传》写这个人物较少正面刻画,而是通过其与曹操的交往来写的。曹操欲“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显示其刚正;立作白雀之文,“操异而奇之”,写其文采;曹操攻城不下,不疑进策而下之,写其武略;最后曹操“心忌不疑,欲除之”的时候,又对曹丕说“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足以显见周不疑的才干非凡:周不疑的事迹完全是以曹操的视角来写的,同时也把曹操从爱才、用才到忌才的心理变化写了出来。这种手法,可以起到正面描写无法替代或者很难达到的书写效果。
4.对比衬托。郡书地记中在进行人物刻画时,有时采用对比衬托的手法。这种手法,有时表现为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如《襄阳耆旧记》: “黄穆,字伯开,博学,养门徒。为山阳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神雀、白鸠之瑞。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秽无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言不同也。”[121]黄穆与其弟黄奂,一个博学有德,另一个却贪秽无行,对比之下,褒贬分明。
有时表现为同一人物在不同方面的特征的对比。如《汝南先贤传》:“周爕,字彦祖,好潜静养志,唯典籍是乐。有先人草庐,庐于东坑其下,有陵田,鱼蛤生焉,非身所耕渔则不食。”[122]这个周爕洁身自好,潜静养志,俨然后世的诸葛亮、陶渊明一类的人物,颇见宁静致远之态。想必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了。可是,《汝南先贤传》却又这样描画了周爕的肖像:“周爕,字彦祖,敛颐折頞,貌甚丑。母欲不举,其父曰:吾闻诸圣贤人状,皆有异于人,兴我宗者,必此儿!遂育之。”[123]原来,周爕却是个长相奇丑,竟然连母亲都不想抚养的丑人。但这并没有妨碍读者对周爕的评价,反而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又如《益部耆旧传》:“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干。刘璋遣诣曹公,曹公不甚礼;公主簿杨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纳。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修以此益异之。”[124]给人特别突出的印象是张松的丑陋的形貌与干练强记的才华的反差。(此外,这里还有张松与其兄张肃在威仪容貌方面的对比,以及杨修和曹操的识见方面的对比)
有时表现为同一人物在不同时间、地点和场合的不同行为或语言的对比。例如,晋白褒《鲁国先贤传》载:“二世时,山东贼起。二世问诸侯曰: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人前曰:人臣无将则反,罪至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辐揍,安有反者!此乃鼠窃狗盗,守卫今捕诛之,何足可忧!二世喜,乃赐通衣帛,拜为博士。诸生或讥通之议,通曰: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随从项梁,梁死从项羽。”[125]叔孙通猜透了秦二世的心理,知道他忌讳“反”字,所以在朝堂之上极尽谄媚之词,而一旦离开朝堂,则感叹“我几不免虎口”,马上逃亡。
有时表现为不同的人物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不同看法。例如,《零陵先贤传》曰:“璋遣法正迎刘备,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曰: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126]刘巴对刘璋苦言相劝,刘璋不听,终遭刘备算计。倒是作为对手的刘备对刘巴的才干倍加欣赏。其后,《零陵先贤传》又有这样的记述:“辅吴将军张昭尝对孙权论巴褊阨,不当拒张飞太甚。权曰:若令子初随世沉浮,容悦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称为高士乎?”[127]刘巴,字子初,才智过人,而不肯随世沉浮,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孙权与张昭对刘巴的不同看法,显现出两人在识见上的巨大差距。
为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写人时,郡书地记也有时采用衬托的手法。如《汝南先贤传》:“薛勤,字恭祖,仕郡为功曹。陈仲举时年十五,为父赍书诣勤。勤顾而察之,明日造焉。仲举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来候之。不从卿也。言议尽日。乃叹曰:陈仲举有命世才,王佐之具。”[128]为了突出少年陈蕃(字仲举)的才华,《汝南先贤传》特意以薛勤对陈蕃和陈蕃父亲的不同态度来作比较,使陈蕃父亲仅陪衬,使陈蕃的形象更加鲜明。
(二)情节内容的安排
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从题材的选择到情节内容的生活化、传奇化、神异化,都体现着其小说因素的加强。
1.以小见大的题材选择。郡书地记中的人物故事,不像正史人物传记那样把关注点放在朝政要事上,而是更多的从日常琐事、生活细节记录描写人物,在题材选择上显示出以小见大的特点。如《汝南先贤传》:“蔡君仲孝养老母。时赤眉乱,君仲取桑椹,赤黑异器。贼问之,答曰:黑者与母,赤者自食。贼嘉之,与盐二升。”[129]正是通过“君仲取桑椹,赤黑异器”这一细节显现的孝顺之心,赤眉军才放过了蔡顺(字君仲)。读者也能通过蔡顺顾及老母牙口不好而采熟桑椹给她这一细节,体会到蔡顺的孝顺和细心。又如《长沙耆旧传》:“徐伟奴善叛,知识欲为伟售之。伟曰:不可,奴往当复逃亡,岂可虚受其价?廉平义正若此。”[130]徐伟不把善逃之奴转售他人,显现了他的忠厚。再如《鲁国先贤志》曰:“孔翊为洛阳令,置器水于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一无所发。弹治贵戚,无所回避。”[131]孔翊执法严明,不徇私情,是通过“置器水于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来写的,显得真实而生动。
2.情节的生活化特点。再现生活化的场景,也是郡书地记中叙写人物故事的一个特点。如《广州先贤传》曰:“罗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邻家牛数入食其禾。既不可逐,乃为断刍,多着牛家门中,不令人知,数数如此。牛主惊怪,不知为谁。阴广求,乃觉是威。自后更相约率检犊,不敢复侵威田。”[132]罗威遇到了到他家田地吃禾苗的牛,不但不驱打,还把牛牵回家,亲自铡草喂养,以此感化了牛主。类似的还有《陈留志》:“范乔,邑人腊,多盗斫其树,人有告,乔佯弗闻,邑人愧而归之。乔曰:乡腊日取此,欲与父母相欢娱耳。”[133]范乔对盗斫其树的乡亲显示出宽容和理解。前面这两则故事都涉及平常生活中邻里关系。又如《陈留人物志》:“范乔,字伯山。年二岁,祖父馨临终执其手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流涕。”[134]这则故事涉及平常家庭生活的亲情关系。
3.情节的神异化端倪。受魏晋时盛行的神仙道术思想影响,郡书地记中也记载了一些神异化的内容。如《广州先贤传》:“顿琦,字孝异,苍梧人,至孝。母丧,琦独身立坟,历年乃成。居丧逾制,感物通灵,白鸠栖息庐侧,见人辄去,见琦则留。”[135]其中“感物通灵,白鸿栖息庐侧,见人辄去,见琦则留”的记述,就明显带有神异化色彩。再如《汝南先贤传》:“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终,棺在堂,西舍失火,火将至,君仲伏尸号哭,火越向东家。”[136]蔡君仲伏尸号哭,竟能感动祝融之神,“火越向东家”。再如《益部耆旧传》曰:“王忳诣师,于客舍见诸生病甚困,谓忳云: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与,收藏尸骸。未问姓名而绝。忳卖金一斤,以给棺殓,九斤置生腰下。后署太度亭长,到亭日,有大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风,有一绣被随风而来。后乘马突入金彦门,彦父见曰:真盗矣。忳说状,又取被示之。怅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马归彦父,彦父不受,遣迎彦丧,金具存。”[137]王忳出任大度亭长,遇到了神奇之事,骏马绣被飘然来前。他上了马后,马却把他驮到了金彦家里。金彦父亲认出了是自家的马,起初还以为王忳是盗马贼,待问明情由,才知道是误会。王忳慷慨助难、不贪钱财的行为,不但得到了骏马绣被的果报,还为自己赢得了美名。这个故事被收入《后汉书·独行传》。以上人物事迹的记述中,已经显露出情节的神异化端倪。
4.情节的传奇化色彩。郡书地记叙写人物故事,受到的思想约束较少,因而作者可以在一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有意的加工修饰,而使其具有某些离奇色彩。例如,《益部耆旧传》记载了一个明察干练、智审疑案的官员:“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旁女子哭声不哀,问之,云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尸,曰:当有物自往。吏白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138]严遵看到一个“夫遭烧死”而“哭声不哀”的女子,心生疑窦,即命仵作探明实情而后审问,才真相大白。“当有物自往”的断言,说明严遵已经把案情料定了八九分。这样的记述,显然带有传奇性。
又如《广州先贤传》:“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阳终宠忧见颜色,常用怪焉。牙造膝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瘁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周张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也。牙乃佣仆自贬,吏役而至于宛陵,与张校圉交通,竭节於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其故,牙因手刃张首而还。”[139]此写尹牙替主报仇的故事,俨然是豫让刺赵襄子故事的翻版。豫让为智伯报仇,“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尹牙也是“佣仆自贬,吏役而至于宛陵”,只是豫让没有成功,而尹牙最后“手刃张首而还”。而其“竭节於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的复仇准备,比豫让刺赵襄子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
郡书地记里还有很多情节传奇化的小故事。如盛弘之《荆州记》:“沔水隈潭极深,先有蛟为害。邓遐为襄阳太守,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丹水,勇冠当时,于后遂无蛟害。”[140]写邓遐太守为民除害之壮勇,通过盛弘之《荆州记》生动的文笔展现出来。又如《零陵先贤传》写刘备智斩杨怀之事:“刘璋请玄德,璋将杨怀数谏。备亦设宴,请璋子祎及怀。酒酣,备见怀佩匕首。备出其匕首,谓曰:将军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观乎?怀与之。备得匕首,谓怀曰:汝小子,何敢闲我兄弟之好邪?怀骂言未讫,备斩之。”[141]刘备先是用计解除了杨怀的武装,再杀之于座,精明果敢的形象,栩栩如生。而就故事的情节看传奇味道浓厚,可以看出,此故事一定经过地记作家加工处理。
(三)叙述语言的文采
就叙述语言来看,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亦颇有文采。其中优不乏语言简洁传神的文笔。如《汝南先贤传》中的两条,其记袁宏:“袁宏,字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辟太尉掾,卒。”[142]用字审慎简洁,绝不拖沓,可谓言简而意丰。其记许慎:“许慎为功曹,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143]语言凝练、含蓄,具有简练清俊的特点。
《长沙耆旧传》的记述语言也很生动。如《长沙耆旧传》直接表明对文学应该特别重视:“太尉李公,时为荆州刺史,下辟书曰:欲采明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学。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于鱼;或百文学不出奇士,不可舍文学求之于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学亦士之场矣。”[144]其记述本身就有较强的文采。“太尉李公”指的是东汉李固。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历太尉,为梁冀构死。他大力提倡援引文学之士,当然有矫正东汉外戚宦官交替弄权局面的用意,但他的这段说辞,还是颇有文学意味的。他以“明珠”与“奇士”、“蚌”与“文学”作类比,突出选贤任能的重要性,比喻新奇而易懂,语言生动而显豁。
为了增加故事的生动性或真实感,朝郡书地记写人记事,有时还在结尾插入一些评语、歌谣等内容以为点缀。例如《襄阳记》:“岘山南习郁大鱼池,依范蠡养鱼法,种楸、芙蓉、菱芡。山季伦每临此池,辄大醉而归,恒曰:此我高阳池也!城中小儿歌之曰:山公何所往,来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145]此写山简(字季伦)逸闻,先交代习郁鱼池的优美环境,再叙山简言语行动以见其放诞情状,最后更以城中小儿歌之渲染强化叙述效果,记述相当精彩。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郡书地记,在叙写人物方面已经显现出相当浓郁的文学色彩了。从题材的选择,情节内容的安排设置,人物形象的刻画,到富有文学意味的语言,其文学性均有体现。程千帆说包括郡书地记的魏晋杂传“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146]。程毅中也说:“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杂传演化而来的。”[147]郡书地记等地方人物杂传,为后代小说写人叙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蓄积着肥沃的养料,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