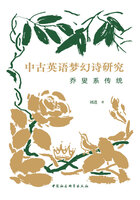
第3章 绪言
梦幻诗和浪漫传奇是中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文类。林奇认为,“梦幻诗与浪漫传奇或许可以并称为时代文类(the genre of the age);再者,人们也许同样可以说,12世纪到14世纪这一时期就是梦幻诗时代(the Age of Dream Vision)”[1]。她引用德国学者丁泽尔巴赫(Dinzelbacher)的统计,指出,“保守计算”,如果不区分文学梦幻诗和非文学梦幻诗,从6世纪到15世纪写作的梦幻诗超过了225首,其中大多数(大概70%)出现在1100年以后,而文学梦幻诗更是90%都出现在1100年以后。[2]林奇的数据包含欧洲大陆和英国这一时期的梦幻诗作,而且包括了梦境(dreams)和幻象(visions),显示了梦幻叙事在中世纪西欧的流行程度。但严格说来,梦幻诗(Dream vision)并不是“梦境与幻境诗”(Dream and Vision),不同于梦境(Dreams),也不同于幻境(Visions),而是一种独立的文类,有着独特的结构、主题和程式。有很多学者都曾试图定义梦幻诗。斯皮林(A.C.Spearing)的《中古英语梦幻诗》(1976)是对英语文学中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梦幻诗的综合性研究。尽管他并不确定梦幻诗能否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文学文类,但他意识到:
梦幻诗的确倾向于某种主题组合:理想且往往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致,在其中做梦人邂逅一个权威人物并从而获取某个宗教或世俗教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从14世纪以降,梦幻诗更加完全地实现了其作为一首诗歌的存在。和其他诗歌相比,梦幻诗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诗歌有开头和结尾(标记是叙事者入睡和苏醒);有叙事者,他的经历构成诗歌的主要内容;诗歌属于想象虚构类(无论将其看作灵感还是空想,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间)。简言之,梦幻诗并非自然之作,而是艺术之作。[3]
斯皮林的定义强调梦幻诗不仅仅包含一些熟悉的主题,如理想景致和通过权威人物揭示教义,更是一件诗人有意识地设计、创造的“艺术作品”:有精心打造的开头(入梦)和结尾(梦醒),有一位敏于观察的叙事者,他的经历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并构成梦境的主要内容。
达维朵芙(Judith M.Davidoff)的《良好开端——中世纪晚期的框架叙事》(1988)一书专章研究“梦幻框架虚构叙事”(“Dream-Vision Framing Fictions”),将梦幻看作中世纪晚期虚构作品的一种重要叙事框架,通过观察和研究43首梦幻诗,她提炼出这些作品中共同的叙事结构,即“虚构框架+梦境内核”:
梦幻诗序言是最常见的一种中世纪虚构框架叙事。如果诗人—叙事者叙述说,在某个情形下,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和一个梦境内核。如果他还叙述了后来梦醒的情形,那么这首诗的叙事框架就是“闭合”的。……
虚构叙事框架是一个短篇叙述,引出(也可能终结)一篇较长的诗作,并为这个核心诗篇提供除自身而外的又一个语境。在中古英语所有的开场技法中,梦幻诗序言最契合这个定义。梦前的材料明显是叙述性的,因为诗人—叙事者几乎总是要讲述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形下他入睡并做梦。当他醒来时,他往往回到开篇的虚构,告诉读者他醒来以后的经历,或梦境对他产生的影响,或他为何要复述这个经历,也可能讲述所有这些内容。……
梦前的虚构框架显示了诗人—叙事者所承受的精神、心理或社会性的压抑。梦境内核以一种说教的方式应对这种压抑,或者至少是与这种情绪多少相关。最后,在梦后情节中诗人—叙事者通常会认为梦境对他起到了教育启迪作用。[4]
达维朵芙的定义重点突出了梦幻诗的框架叙事特征,这也就是斯皮林提及的“开头和结尾”:诗人—叙事者会描述入睡前的情形,通常也会叙述梦醒后的场景。梦前、梦后的叙述将梦境内容置于一个“闭合”的叙述框架中。达维朵芙还指出了这个虚构的叙事框架与梦境内容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梦境内容往往会呼应诗人—叙事者梦前的心绪,有时候诗人—叙事者会在梦境中找到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或至少得到一些慰藉。
拉塞尔(J.Stephen Russell)在其关于梦幻诗的精彩论著《英语梦幻诗——形式解析》(1988)中对梦幻诗进行了深度“解析”,详尽阐述了梦幻诗的相关理论、起源和结构,并以《公爵夫人书》、《珍珠》和《声誉之宫》为例分析了中世纪晚期诗人对梦幻诗结构和话语的解构式应用。在“引言”中,拉塞尔对梦幻诗进行了定义和描述:
要成其为梦幻诗(或者其他某类既定的诗),一首诗必须既包含某些母题(motifs),又体现诗人刻意追随某个传统或者模仿某个文类范式的意图。……
中世纪没有专门的词汇描述这一类诗歌,但实际考察一下这些梦幻诗的结构或者形态,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刻意的设计而不仅仅是一些母题的集合。在最简单的层面上,梦幻诗是对梦境的第一人称叙述;通常情况下,梦境描述之前有一个序言引出做梦人这个角色,之后则有一个后记描述做梦者梦醒并以诗行记录梦境。序言往往短小含蓄,是梦幻诗中最程序化和公式化的部分。除了构建叙事框架,序言的作用还在于塑造做梦人/诗人的人物特征。在序言中,读者常常可以看到做梦人心情郁闷或者因为一个未指明的问题忧虑或担心,以至于夜晚难以入睡。……
在这部分介绍性的框架叙事之后,开始了梦境报道。梦境通常记录一场辩论或者一场不那么正式、与一个或多个人物的谈话,有时是真实人物,有时是寓意人物。……
这个梦境报道构成诗歌的主要内容,诗歌结尾处往往有一个简短的后记框架描述做梦人从梦中醒来,个别诗歌还会对梦境报道进行阐释性的评述。……就像十四行诗最后的对句一样,梦幻诗的结尾强调了这件艺术品的点睛之笔,激发读者关注其艺术性的收尾。[5]
拉塞尔的定义最为全面准确地描述了梦幻诗的结构特征,不仅指出“梦幻诗是对梦境的第一人称叙述”,还提炼出梦幻诗“序言—梦境报道—后记”的叙事框架,也简要提及了梦幻诗的一些母题特征。
从上述斯皮林、达维朵芙和拉塞尔对梦幻诗形式和结构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梦幻诗”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包含梦境或者幻境的诗歌。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文学,还是希伯来—犹太圣经文学,抑或晚近的宗教、世俗文学,关于梦境的叙述数不胜数,但是就像拉塞尔指出的那样,必须区分“作为叙事事件的梦境”(the Dream-as-Narrative-Event)、“幻境(像)”(Visions)和“梦幻诗”(Dream Vision)。[6]“作为叙事事件的梦境”是第三人称叙事,就像催化剂一样推动情节发展。“幻境”是宗教性的,具有启示意义(因此拉塞尔称之为“启示”或“启示幻境”),以第三人称叙事居多,经历幻境获得启示的人通常并没有入睡。在英语中,《十字架之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是最早出现的梦幻叙事,此外,古英语文学中还有基涅武甫(Cynewulf)的《埃琳娜》(Elene)和比德(Bede)所记录的《凯德蒙之梦》(Caedmon's Vision)等幻象叙事诗作。但是,英语中真正的“梦幻诗”在14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写作了多部梦幻诗,如《公爵夫人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声誉之宫》(The House of Fame)、《百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和《〈贞女传奇〉序言》(Prologue to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头韵体文艺复兴运动诗人也创作了大量梦幻诗,如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的《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和“戈文”诗人(the Gawain Poet)的《珍珠》(Pearl)。纵观这些诗歌,结合前述三位学者的定义,可以得出结论,严格意义上的梦幻诗通常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由“梦前序曲—梦境—梦醒后记”几个环节构成基本叙事框架;有的作者会在此基础上做出调整,比如《农夫皮尔斯》可以说多次重复了“入梦—梦境—梦醒”这个过程。
(二)梦前序曲着重刻画叙事者—做梦人,他的思虑、渴望和疑惑与梦境呼应,换言之,梦境回应了做梦人的现实欲望。
(三)梦境内容可能是对话、辩论、集会、旅行,叙事者—做梦人很多时候处于观望者状态,他可能会看到动物谈话、得到神明指点、邂逅寓意人物,或者与真实人物交流;权威人物的指引颇为常见,虽然并不是必然;也有叙事者—做梦人作为梦境中事件的主角出现。
(四)理想景致,无论出现在天上还是人世,是一个常见的梦幻诗母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前文林奇所统计的“从6世纪到15世纪的梦幻作品”属于广义的梦幻诗作传统,而狭义的梦幻诗传统滥觞于法语梦幻诗。在伟大的《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以及其他法国诗人影响下,乔叟和他的同龄人开启并巩固了英语梦幻诗传统,在随后的15、16世纪,在伦敦、西北中部地区和苏格兰的诗人延续了英国文学中的梦幻诗传统。达维朵芙关于“梦幻虚构叙事框架”一章的研究对象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43首英语梦幻诗,她将这些诗歌按照主题分成三个类型:一是爱情寓意诗,主要包括乔叟译《玫瑰传奇》,《公爵夫人书》、《百鸟议会》、《〈贞女传奇〉序言》、《丘比特之书》(The Boke of Cupide)、《玻璃神庙》(The Temple of Glass)、《国王之书》(The Kingis Quair)、《淑女之岛》(The Isle of Ladies)、《淑女集会》(The Assembly of Ladies)、《荣誉殿堂》(The Palice of Honor)、《金色盾牌》(The Goldyn Targe)和内维尔《享乐城堡》(William Nevill,The Castell of Pleasure)等;二是宗教、道德梦幻诗,主要包括《肉体与灵魂》(Body and Soul)、《珍珠》、《农夫皮尔斯》、《三代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ree Ages)、《死与生》(Death and Life)、利德盖特《夜莺发言》(John Lydgate,A Seying og the Nightingale)和邓巴(William Dunbar)的一些宗教梦幻短诗等;三是政治、社会和热点题材梦幻诗,主要包括《聚敛者与挥霍者》(Winner and Waster)、《学士与夜莺》(The Clerk and the Nightingale)、《加冕之王:统治的艺术》(The Crowned King:On the Art of Governing)、《刺蓟与玫瑰》(The Thrissil and the Rois)、邓巴的几首政论梦幻诗等。达维朵芙自己也认识到这三类梦幻诗之间的“交叉重合”,她试图增加一类“包罗广泛的梦幻诗”(“broadly inclusive dreams”),把诸如英译《玫瑰传奇》《农夫皮尔斯》《声誉之宫》《贞女传奇》《荣誉殿堂》等归入此类。达维朵芙所整理的43首梦幻诗作不仅涵盖了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重要的梦幻诗作品,还包括一些不为人熟知的篇章,为梦幻诗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语料参考,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诗篇中竟然没有斯凯尔顿(John Skelton)的作品,无论是《朝廷恩宠》(The Bowge of Court),还是《月桂冠冕》(The Garland of Laurel),都没有出现。此外,她的分类也存在问题。虽然她声称第四类中有几首诗已经列在了前面三类的某一类当中,但我们并没有找到《声誉之宫》的身影。这恰好证明,她的主题分类法并不能很好地将这些梦幻诗进行有效的分门别类。相比之下,还是比她早十多年研究梦幻诗的斯皮林给出的分类更具可行性。斯皮林指出:
从乔叟在世直到16世纪早期斯凯尔顿(Skelton)的作品,大多数梦幻诗都属于一个大致可以称作“乔叟系”的传统。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大批头韵体梦幻诗,全是佚名作品。15、16世纪的苏格兰也涌现出不少梦幻诗,既有非凡之作,也有不入流之作,诗人包括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亨利森(Henryson)、邓巴、道格拉斯(Douglas)和林德赛(Lindsay)。[7]
基于此,他在书中将中古英语梦幻诗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研究:首先是乔叟的四部梦幻诗;其次是头韵体传统,包括《珍珠》和《农夫皮尔斯》及其他归于《农夫皮尔斯》传统的头韵体梦幻诗,如《聚敛者与挥霍者》、《三代议会》、《沉默与谏言》(Mum and the Sothsegger)和《死与生》;最后是乔叟系传统,包括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乔叟系诗人的梦幻诗作品,如利德盖特《玻璃神庙》、约翰·克兰沃爵士《布谷鸟与夜莺》(Sir John Clanvowe,The Cuckoo and the Nightingale)[8]、詹姆士一世《国王之书》,在乔叟《〈贞女传奇〉序言》影响下苏格兰诗人的梦幻诗序言(dream-prologues),邓巴的大量梦幻诗,主要包括《刺蓟与玫瑰》和《金色盾牌》,道格拉斯《荣誉殿堂》以及斯凯尔顿的两部作品《朝廷恩宠》和《月桂冠冕》。斯皮林的分类注重梦幻诗的不同传统,从乔叟及乔叟系梦幻诗和头韵体梦幻诗两条线考察英语梦幻诗,可以很好地覆盖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多数梦幻诗。这种分类法也凸显了乔叟和乔叟系诗作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主流地位,相对而言,头韵体诗歌则属于“遗失的传统”,意思是说,这个在1340年前后不明原因突然复兴(说“复兴”是因为头韵体这种诗歌形式可以追溯到此前近1000年,而且曾在盎格鲁-萨克逊时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的诗歌传统在经历不到200年的繁荣之后,于16世纪早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曾重现。[9]斯加特古德(John Scattergood)用“遗失的传统”为自己关于中古英语头韵体诗歌的研究论文集命名,他在“序言”中引用上述斯皮林的论断之后提到,尽管20世纪一众诗人,其中有庞德和奥登,试图复兴头韵体诗歌,但是这一传统实实在在是“遗失”了。[10]从头韵体梦幻诗传统来看,可以确知《珍珠》和《农夫皮尔斯》创作于14世纪后半叶,而《聚敛者与挥霍者》和《三代议会》虽然创作时间不明,但有可能早于《农夫皮尔斯》,《沉默与谏言》主题是理查二世的朝政,很可能也是14世纪末或者15世纪初的作品;《死与生》是这些作品中最晚出现的一部,但也可能作于15世纪早期。由此可以看出,头韵体英语梦幻诗只是在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间昙花一现。但是,与之相应的乔叟系梦幻诗却一直延续到16世纪,在苏格兰乔叟系诗人邓巴和盖文·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和英格兰乔叟系诗人斯凯尔顿、斯蒂芬·霍斯[Stephen Hawes,著有《德行模范》(The Example of Virtue);《快乐消遣》(The Pastime of Pleasure);《恋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Lovers)]、威廉·内维尔(《享乐城堡》)等人的作品和佚名诗作《智慧殿堂》(The Court of Sapience)中俨然出现了一个小阳春。斯皮林的研究包括了从最早的乔叟系梦幻诗《布谷鸟和夜莺》,到15世纪利德盖特的《玻璃神庙》和詹姆士一世的《国王之书》,再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邓巴、盖文·道格拉斯和斯凯尔顿的一系列梦幻诗;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专门研究了苏格兰乔叟系诗人在《〈贞女传奇〉序言》影响下创作的“梦幻诗序言”,即将梦幻诗作为一部长诗的序言部分。他省略了缺乏趣味和创意的霍斯与内维尔的诗作以及不完整的《智慧殿堂》,这可以理解,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竟然完全没有提及《淑女之岛》这部非常重要且有趣的梦幻诗,关于《淑女集会》他也只是草草带过,对于与梦幻诗传统渊源深厚的“无梦之梦幻诗”《花与叶》(The Floure and the Leafe)也未曾着墨。本书以斯皮林的分类为基础,以乔叟同龄人克兰沃的梦幻诗《丘比特之书》为乔叟系梦幻诗开端,到利德盖特《玻璃神庙》、詹姆士一世《国王之书》《花与叶》《淑女集会》《淑女之岛》,最后研究邓巴《刺蓟与玫瑰》和《金色盾牌》,斯凯尔顿《朝廷恩宠》和《月桂冠冕》,考察乔叟系梦幻诗的特征和演变。
尽管斯皮林《中古英语梦幻诗》一书中“乔叟系传统”(The Chaucerian Tradition)独成一章,他并没有明确定义“乔叟系”,只是简单写道:“众所周知,乔叟作品对15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诗人影响巨大而广泛;其他文学形式如此,梦幻诗亦如此。”[11]虽然他认为“在‘乔叟系’梦幻诗中,同更广泛的乔叟系作品一样,区分真正理解乔叟创作意图的作者和不得其要领的作者十分重要”[12],但可以看出他对“乔叟系”的定义大概就是指受到乔叟影响而写作的诗人或者在乔叟作品影响下写成的诗歌。不过,这个定义其实十分含糊,比如,到底什么是“乔叟影响”?今天的读者提到乔叟,首先会想到的是《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但是刘易斯(C.S.Lewis)指出,“当14、15世纪的人们想到乔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坎特伯雷故事》。他们心目中的乔叟是写作梦幻诗、寓言、爱情罗曼司和爱情辩论诗的乔叟,是文辞精妙、崇德尚礼的乔叟”[13]。珀索尔(Pearsall)也提出:“英格兰乔叟系诗人对乔叟的态度不同于我们。现代批评家称颂乔叟的幽默、现实主义和反讽、对人物品格的敏锐,赞美他观察的广度和精确、复杂的叙事态度和饶有趣味的叙事者;15世纪几乎异口同声地夸赞他的说教劝诫、风格技巧和修辞雄辩。对于利德盖特而言,他是‘高贵的辞令家,无所不长’,对于霍克利夫他是‘辞令之花’……”[14]事实上,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的文人圈里,乔叟被誉为“伟大的译家”(法国诗人德尚,Deschamps)、“维纳斯的诗人”(高尔,John Gower)、“高尚的哲理诗人”(汤姆斯·乌斯克,Thomas Usk)、“崇高的修辞家”(利德盖特)、“尚德的乔叟”(司克根,Henry Scogan)以及“辞令之花”(汤姆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15]人们推崇的是他书写的爱情、哲理以及他对英语语言和文学形式的改进,而这些元素大多体现在他的译作《玫瑰传奇》和《博伊斯》(Boece)、《特洛伊勒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骑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四部梦幻诗和一些短诗,如《马尔斯怨歌》(The Complaint of Mars)、《致罗莎蒙德》(To Rosemounde)等之中。因此,何为“乔叟影响”其实很难定义。
另一位中世纪学者海伦·菲利普斯(Helen Phillips)则不太赞同从“影响”或“模仿”出发定义“乔叟系”。她指出:
“乔叟系”诗歌不是一个精确的术语。将之简单定义为模仿乔叟的诗歌既太过宽泛,又太过狭窄。从批评角度看,最好是将之视为一个大传统下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次类别:爱情叙事诗传统(dit amoureux)以及相关的抒情诗文类,这个传统13世纪在法国兴起,在乔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持续在海峡两岸繁荣发展。从历史角度看,有关乔叟系诗歌的价值和类似乔叟的作品包括哪些,学界往往观点不一。在当今的“批评”实践中,“乔叟系”通常指的是乔叟从法语引入英语的那些抒情诗形式,尤其指怨诗、歌谣、诗跋,以及抒情—叙事诗:即框架叙事诗,这些诗歌的题目中一般都包括朝堂、梦、宫殿、庙堂、议会、丘比特、爱情、淑女一类词汇,在中世纪晚期和都铎朝的乔叟和其他诗人诗歌选集中占据很大比重。从结构来看,这些诗歌在一个或者多个框架中包含一个内核,或抒情,或辩论,或叙事(往往包含寓意)。[16]
菲利普斯的定义具体指出了乔叟系诗歌的法语源头,强调了乔叟系作品的主要形式是抒情诗和框架叙事诗,她所列举的标题中的常见词汇显示了“宫廷”和“爱情”在乔叟系诗歌中的突出地位。虽然菲利普斯并未专程定义乔叟系梦幻诗,但乔叟系诗歌与法语诗歌的渊源最主要体现在乔叟系诗人对《玫瑰传奇》和《玫瑰传奇》影响下创作而成的一系列法语梦幻诗的解读和借鉴。《玫瑰传奇》虽然并不是法语中的第一首梦幻诗,[17]却是中世纪欧洲影响最大的梦幻诗。诗歌包括吉约姆·德·洛里(Guillaume de Lorris)的原作(4058行)和大概40年之后由让·德·莫恩(Jean de Meung)完成的续作(17732行),在当时风行一时,共有约250个手抄本流传于世。乔叟和沃尔顿(Walton)曾将《玫瑰传奇》的一部分翻译为英语,这无疑增加了其在英语诗人间的影响力。《玫瑰传奇》的梦境设定、尘世乐园、风雅爱情、寓意人物成为梦幻诗的固定程式,莫恩部分的反讽、哲理和百科全书式的叙事也对乔叟和乔叟系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法国诗人马修(Guillaume de Machaut)、德尚、福瓦萨尔(John Froissart)等创作的爱情叙事诗和梦幻诗也是乔叟写作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无论是乔叟本人,还是乔叟系诗人,当他们试图从法语诗歌中汲取养分、寻找灵感的时候,所接触到的很多作品都是梦幻诗,而且是以“风雅爱情”为主题的梦幻诗;这些诗歌形式考究,语言典雅,书写对象是精致风雅的宫廷文化和爱情;无论是“庙堂”(维纳斯神庙),还是爱情朝堂,抑或宫殿、岛屿,都是基于现实却更加理想化的王廷。由于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宫廷文化对英国贵族影响颇深,法语语言和文学也是英国诗人竞相模仿学习的对象,所以菲利普斯将乔叟和乔叟系诗歌看成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蔓延发展的爱情叙事诗传统的一个分支也不无道理。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乔叟系诗人,特别是晚些时候的乔叟系诗人很可能并没有直接从法语文学中寻找灵感,而完全是借由乔叟的诗歌继承了这一源于法国的爱情叙事诗传统。
茱莉亚·柏菲(Julia Boffey)在其编撰的《十五世纪英语梦幻诗选集》引言中也称“乔叟系”这个术语颇难界定:因为传统上被认为是“乔叟系”的作者们各有不同的兴趣和背景,采用的语言也可能并非乔叟所使用的伦敦英语;基于柏菲选集中的作品,即《玻璃神庙》、《国王之书》、奥尔良的查尔勒《爱的接续》(Charles of Orleans,Love’s Renewal)、《淑女集会》和斯凯尔顿《朝廷恩宠》,她认为“乔叟系”梦幻诗的一个特点在于“这些诗作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指涉乔叟,并以某种方式明确宣布它们与某个与乔叟名字相联系的特定写作传统之间的联系或偏离”,因此,柏菲认为定义乔叟系梦幻诗最好的办法就是参考乔叟本人的梦幻诗,因为这些诗歌尽管主题和风格各有意趣,但也有不少共同特征。[18]关于乔叟本人的梦幻诗,柏菲很有洞见地指出,他的四部梦幻诗“都或多或少关注了世俗爱情”,而且“讨论爱情的背景都关乎‘宫廷’,反映了那些有闲暇时光培育和讨论人际关系的人们的兴趣:即贵族和社会特权阶级,他们的世界实际上糅合了国会、宫廷和贵族世家,这些乔叟都有所记述。这些人熟知狩猎一类的活动(《公爵夫人书》)、户外庆典(《百鸟议会》和《〈贞女传奇〉序言》)、追名逐利(《声誉之宫》),也能用行家的眼光欣赏令人愉悦的美好花园、庙堂、挂毯和壁画”[19]。由于柏菲本人常年致力于乔叟系梦幻诗整理编撰和研究,她的定义抓住了“乔叟系”梦幻诗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这些诗歌有意识地指涉乔叟诗歌,换句话说,乔叟的梦幻诗为它们提供了相关历史、文学背景和写作素材;二是这些诗歌与“宫廷”之间的联系很密切,也就是说,乔叟系梦幻诗大多数属于“宫廷文学”范畴,反映了王公贵族的风雅诉求或者朝堂生活。
乔叟梦幻诗的法语源头决定了其与“宫廷”(court)的密切联系和“风雅”(courtly)特性,加上乔叟本人长期效力于英国王室,甚至有可能他曾经在王室聚会上朗读自己的诗歌,他的诗作,特别是早期诗作,都可以称作“宫廷诗歌”(court poetry)。关于“宫廷诗歌”,需要做两个方面的说明。首先,用中文“宫廷”翻译英文“court”其实并不能完整传达“court”的意义。道格拉斯·格雷(Douglas Gray)在评述中古英语诗歌《爱情朝堂》(The Court of Love)之时特别指出了“court”的三层意思:“由一名女王主持的社交集会(social court),恋人在此获取关于恋爱礼仪和法则的指导;由一名法官主持的法庭,可以在此提起诉讼、抗辩,并进行裁决、处罚;由君主引领的封建王廷,人们必须效忠君主。”[20]而乔叟的“宫廷诗歌”往往糅合了“集会”“法庭”“王廷”这三层意思。在《声誉之宫》中,恢宏的声誉殿堂之上,声誉女神高踞宝座,求取名声的芸芸众生集聚一堂向女神诉说求告,声誉女神随心所欲分派“名声”。《〈贞女传奇〉序言》中,爱神、王后以及众多随从侍女汇聚一处,对叙事者进行控诉裁决。《百鸟议会》中,在记叙自然女神主持的百鸟集会之前,乔叟也简要描述了维纳斯女神的爱情神庙,呈现了恋人跪在女神面前求告的场景。《公爵夫人书》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某个王廷,但在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却是最典型的“宫廷诗歌”,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这首诗是一首悼亡诗,是为了纪念冈特的约翰的妻子布兰茜去世而作;其二,这首诗最集中地体现了中世纪宫廷文化中的“风雅爱情”,直接反映了王公贵胄的风雅意趣。
其次,理解“宫廷诗歌”需要清楚court poetry(宫廷诗歌)和courtly poetry(风雅诗歌)之间的关系。珀索尔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诗歌》一书中曾专章讨论“宫廷诗歌”,但是他也注意到“宫廷诗歌”这个术语可能过多强调了“宫廷”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
“宫廷诗歌”一词暗示了社会环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文学背景渐趋复杂,使得这种关系始终难以界定。“宫廷”自身就是一个没有固定形态的社会组织,不同的诗人对宫廷的依赖程度也不同。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风雅诗歌”(courtly poetry)这个术语,即表达与宫廷社会密切联系的价值观的诗歌,似乎比“宫廷诗歌”更适合,因为“风雅诗歌”并不强调直接的社会关联。[21]
厘清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乔叟的“宫廷诗歌”其实包含多重内容,既包括以宫廷(上文中广义的宫廷)为背景的诗作、为王公贵胄写作的诗歌,即狭义的“宫廷诗歌”,也包括反映王侯贵族价值观和情感意趣的诗作,即“风雅诗歌”。而乔叟系梦幻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正在于它们都属于广义的“宫廷诗歌”,无论是否以风雅爱情为核心题材,都反映了中世纪王侯贵族的文化意趣,折射出诗人与王廷的关系,有时甚至呈现廷臣之间的争斗。
“风雅爱情”以及与之相伴的骑士精神、礼仪风范是宫廷文学的显著特征,也是乔叟系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宫廷文学的起源,查尔斯·马斯卡廷(Charles Muscatine)在其重要著作《乔叟与法国传统——关于风格和意义的研究》中有所表述,他指出,中世纪宫廷文学滥觞于12世纪的法国,是“对当时上流社会新兴的情感意趣和审美态度的呼应”:
当时地方贵族门庭(provincial court)的骑士、贵妇淑女和教士似乎突然获取了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全新认知,也意识到了自身理想的精致和独特。他们日益远离那些阅读史诗和圣徒传奇的基督徒,使得一个贵族和世俗化的文学应运而生。看起来他们的确发现了或至少是激进地改变了这个文学的主要题目——风雅或浪漫爱情,礼节,骑士风范——并要求他们的诗人创造出合宜的文学风格。到12世纪末,这种态度广泛传播,风格几乎完全成型,一个独立、绵延的宫廷文学传统就此形成。[2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和冒险是法语宫廷文学的两大主题,但是马斯卡廷指出,由于骑士冒险的原动力在于赢取淑女的爱情,“爱情是冒险的理由,而骑士精神是赢得爱情的手段”,所以逐渐地,冒险本身的意义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骑士愿意接受爱情考验,努力追求完美,力争达到最理想的风雅品质。这样一来,爱情就不再是优良品质的回报,而本身就是优良品质的象征。由于这一转变,在晚近的一些浪漫传奇中,爱情,或者是伴随少许冒险的爱情,成了唯一的主题。这在吉约姆·德·洛里的《玫瑰传奇》中尤其突出。[23]在《玫瑰传奇》中,骑士外在的冒险行为转化成内在的情感经历,骑士追求爱情之路上的考验由一系列寓意人物执行,反映了爱情体验中复杂的心理活动。在《玫瑰传奇》和13、14世纪其他法语梦幻诗影响下,乔叟梦幻诗和乔叟系梦幻诗都在阅读或梦境背景下“静态”地关注情感经历。《公爵夫人书》中对于爱情的叙述全是通过叙事者和黑衣骑士的对话或者黑衣骑士的怨歌呈现的;《丘比特之书》通过梦境中夜莺和布谷鸟的辩论探讨爱情;《玻璃神庙》中利德盖特在梦境中于维纳斯神庙内追随女士和骑士的爱情故事;《国王之书》中詹姆士一世身陷囹圄,他从牢房窗户望出去,见到一见钟情的心上人,经历了求爱无望的绝望和“改变命运”的梦境;《金色盾牌》中邓巴在玫瑰花丛中入睡,梦境中经历了理性和爱情的冲突。正因为绝大多数梦幻诗倾向于静态描述和场景铺陈,结合了浪漫传奇的精彩冒险和梦幻诗的细腻情感的《淑女之岛》在乔叟系梦幻诗中独具一格。
法国文学,特别是法语梦幻诗中的“风雅爱情”通过乔叟的梦幻诗《骑士的故事》《特洛伊勒斯和克瑞西达》以及一些短诗,通过利德盖特的《玻璃神庙》和《黑衣骑士怨歌》(The Complaint of the Black Knight),对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学影响甚巨,这一时期大量梦幻诗以“风雅爱情”为主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雅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化生活、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逐步成为“远去的传说”:15世纪后半叶的乔叟系诗歌《无情淑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y)和《爱情朝堂》中就不乏对“风雅爱情”的戏仿和暗讽。早在14世纪,乔叟本人就表达了对“风雅爱情”模棱两可的含混态度。[24]而纵观乔叟系诗歌,可以注意到“风雅爱情”式微的清晰脉络。最初的乔叟系诗歌,克兰沃的《丘比特之书》中已经暗示了对“风雅爱情”的怀疑;《花与叶》并未专门关注“风雅爱情”这一主题,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宫廷生活;《淑女集会》虽然宣称女子集会的目的在于让女子们申诉在爱情中受到的委屈,但从诗歌本身来看,诗人关注的焦点更在于宫廷建制和宫廷日常;《刺蓟与玫瑰》主要是一首纪念国王婚事的“应景诗”,是邓巴作为宫廷诗人的分内之作,内容也并不以爱情为主,而是礼赞婚礼并向国王谏言;《金色盾牌》中叙事者被爱情攻击、俘虏,“理性”遭到驱逐,最终落得寂寥痛苦;16世纪初斯凯尔顿的两首梦幻诗都没有以“风雅爱情”为主题,《朝廷恩宠》讽刺宫廷中廷臣倾轧的现状,《月桂冠冕》的主题则是诗名,尤其是斯凯尔顿本人的诗名。
但是,从上文的概述中也可以看出,即使主题不是“风雅爱情”,乔叟系梦幻诗仍然主要以“宫廷”或广义的“朝堂”为背景,以宫廷文化或宫廷生活为关注对象。没有明确指涉王室的《丘比特之书》在结尾处暗示了理查德二世的王后安妮的寝宫(第284—285行);《玻璃神庙》呈现了维纳斯的朝堂;《国王之书》中叙事者在梦中先后来到了维纳斯、密涅瓦和命运女神的朝堂;《淑女之岛》中呈现了女王统治的女儿岛和爱神的朝堂;《淑女集会》中描述了“忠贞夫人”的朝堂;邓巴本人是苏格兰王廷的“宫廷诗人”,他的《刺蓟与玫瑰》描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和他的大婚,而《金色盾牌》中则描摹了维纳斯和丘比特的朝堂;斯凯尔顿与都铎王廷联系紧密,他的《朝廷恩宠》讲述叙事者在“无双夫人”朝廷的遭遇,反映了宫廷争斗,《月桂冠冕》中呈现了声誉女神和帕拉斯夫人的朝堂。
虽然乔叟本人的梦幻诗关注“风雅爱情”主题和宫廷文化,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局限于宫廷主题。他对爱情的讨论并不局限于“风雅爱情”,比如《百鸟议会》中,通过梦幻框架中马克罗比乌斯《西比奥之梦》(Macrobius,The Dream of Scipio)中的“鄙弃此世”哲学与梦境中维纳斯与自然女神的并置,他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爱情。此外,《声誉之宫》包罗万象,涵盖了爱情、哲学、诗歌、修辞等内容,其中对名声的探讨直接影响了斯凯尔顿《月桂冠冕》的创作,盖文·道格拉斯内容丰富的《荣誉殿堂》也明显地体现了《声誉之宫》的影响。
概括起来,除了具备梦幻诗的一般特征以外,乔叟系梦幻诗的特点如下:
(1)对梦幻诗传统,尤其是乔叟梦幻诗的指涉;
(2)大多数乔叟系梦幻诗以宫廷文化或“风雅爱情”为主要内容,往往以某个君王或者神祇的朝廷为梦境背景,具有明显的“风雅”或“宫廷”特质(courtly);
(3)《声誉之宫》中的哲学、诗歌、声誉主题成为一些乔叟系梦幻诗的写作灵感。
本书研究的十部梦幻诗作品,时间跨度为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也是英国文学史上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丘比特之书》是乔叟系梦幻诗的开山之作,虽然短小,却意趣复杂,深得乔叟梦幻诗精髓。《玻璃神庙》是15世纪最重要的“乔叟学徒”利德盖特的作品,利德盖特诗作在15世纪的广泛传播进一步扩大了乔叟的影响力。《国王之书》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作品,从诗歌结构到主题再到思想深度,都是15世纪难得一见的佳作,可惜由于作品流传不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回音。《花与叶》和《淑女集会》两首诗的叙事者都是女性,诗歌紧凑精巧。《花与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梦幻诗,但由于其对梦幻诗传统的刻意指涉以及与乔叟梦幻诗之间的密切关联,笔者将其列为“无梦之梦幻诗”进行研究。《淑女集会》的梦幻框架层次复杂,内容看似简单,却由于叙事者的闪烁其词增加了解读难度。《淑女之岛》包含两个内容连贯的梦境,且糅合了浪漫传奇和梦幻诗传统,两对恋人的爱情故事绵延交织,情节曲折跌宕、生动有趣。几乎同时代的分别效力于英格兰王室和苏格兰王室的斯凯尔顿和邓巴各自贡献了两首乔叟系梦幻诗,他们的诗歌将乔叟系梦幻诗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