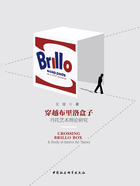
二 相对主义与开放性
1.尼采:开放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19]
当黑格尔的宏观历史哲学把个体融入普遍历史性的海洋中时,尼采则用“超历史”点燃了个体在历史中的绝对优先权。所谓“超历史”就是强调个人价值的信仰,将历史视为充满张力的任意性的集合,历史在此任意性中生长和消亡。因此,“‘超历史’不仅反对历史的思辨哲学,也反对启蒙的理性主义”[20]。尼采采用“视角主义”原则建构他的历史哲学。尼采的视角主义主要讨论认识问题和存在问题,认为任何认识都有视角,眼睛有着自身对外界的解释力和创造力。认识就是我们的情感和冲动对外界做出的解释,是对条件的确认和领悟,而视角就是生命的条件,生命则是视角的存在。[21]
丹托在1965年的著作《作为哲学家的尼采》(Nietzsche as Philosopher)中专门谈论了尼采的视角主义。他认为,视角主义的缺陷在于“它是自我矛盾的,虚无主义的,甚至是唯我论的”[22]。然而,视角主义对日后丹托的历史哲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相当明显,尤其在于它确立了丹托的一个重要立场:开放性。
反省尼采的“超历史”观点,可以看到,尼采以一种开放的精神来反思历史。他密切关注人类的生活和人类历史的精神。他认为,正是通过这些方面,人们得以展示他们的自由,也能看到他们自身在知识上的缺陷。由此,尼采提出“视角主义”原则,认为不存在没有被阐释过的“事实”或“真相”。阿伦·D.施瑞夫特认为,视角主义不是一种本体论的立场,而是“认识论”的立场,通过视角主义,尼采意在向我们揭示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从而为传统认识论中的知识观提供了新的思路,并摆脱了知识是固定不变的成见。同时,“视角”还带来了“阐释”问题。尼采区分了“视角”与“阐释”:前者是给定的视域,超出了我们控制;后者则是以某种方式对许多各不相同的视角进行组织的行为。总之,“视角主义”告诉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以及如何知道,在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新方法时,也从“经验上”对人类的有限性做出概括,即人们对知识的领悟是有限的,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进行评价。据此,尼采还将“视角主义”分成生理的、直觉的和社会历史的三种类型。生理视角指受感觉器官支配的视角,尼采认为人们不可能摆脱这种视角,因为它贯穿在价值判断的选择行为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都将受其限制。鉴于我们的感官能力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力,由此,尼采认为我们缺少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或者“真理”的器官。生理视角之外,则是本能视角,它包含着欲望、需求、感触等本能冲动,因此,“知识”被视为本能冲动的天敌。尼采意识到,知识实际上是本能互动的某种行为,每一种本能冲动都有自己的视角,并试图让自己成为观念判断的准则。此外,“社会历史视角”使得本能视角受到限制,这一视角的形成同个体的生活经历及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虽然尼采一直强调视角的个性化与独特性,不过,他始终没有忽视历史、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并着力批判那些为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丢失历史感的哲学家。
总体说来,视角主义旨在反对传统哲学过于简化知识的做法,同时,视角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视角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需的,而且是‘错误’的。”[23]虽然视角的必要性是虚假的,不过,尼采通过让视角聚焦到“生命的价值”,从而弱化了视角的“真假”问题。“视角主义”在重估价值中的作用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对“知识”的视角化,视角主义解构了传统的认识论赋予客体以“给定性”的看法;另一方面,视角主义又丢弃认识论的客体,使得阐释能够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可以说,视角主义以其多样性的主张来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论错误。
此外,虽然语言学的客观性与视角主义相对,不过,尼采认为,语言学家必须要实现在古代、现代与他自己三者间的理解。这样,尼采就涉足古典语言学领域。正是基于这点,丹托把尼采看作一位分析哲学家。然而,由于语言学力图建构一种客观的科学,其标准为诚实和公正,因而,似乎与尼采的视角主义对知识的描述相矛盾:一方面,语言学阐释要求用科学的阐释对待文本;另一方面,视角主义则要求自由并富有创造性地改造文本。这便引发了相对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冲突。为此,尼采引入了新“客观性”的概念,调解这种矛盾冲突:
应当理解为一种能力,它能支配自己的赞同与反对的意见,让自己公开与封闭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人们就知道如何利用不同的观点和情绪解释来促进认识。……我们越是让对一件事情的各种不同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就会对同一件事情使用更多的不同眼睛,于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更加全面。[24]
这就是尼采的谱系学(genealogy)。它不仅能满足视角主义的多样性,而且还使用严谨的语言学关注文本。不过,谱系学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承认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以“强化生命”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区分“好的阐释”与“坏的阐释”[25]。
2.沃尔什:配景理论[26]
在上文,我们谈到,沃尔什提出了与思辨历史哲学相对应的分析历史哲学的概念,展示出关于知识论的历史学,由于分析历史哲学远离对历史性质的研究,因而从客体回归到主观历史之上。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兼顾了思辨和分析两方面。他把历史学的思维方法总结为“综合方法”,即“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方法来解释那个事件”[27]。即对历史的理解依赖于每个人思想的不同,而对思想的追根溯源又是从每个历史学家自身的哲学观出发。此外,沃尔什也注意到历史学的双面性:科学性和艺术美学性。他提出:“历史学家们还要诉之于什么其他的解释过程呢?……看来很清楚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半科学类型的解释,包括把普遍原则运用于特殊的情况。”[28]
贯穿沃尔什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为:“对于历史的理解或解释,有赖于历史学家对于人性的概括和总结——这里面既包括有经验的成分,也有先验的成分(大体上相当于人们做出了什么和人们应该做出什么这两个部分)。”[29]这种观点引发人们的疑问:历史本身解释的有效性以及历史事实本身的依据,并指向两种长期对峙的理论:一种是客观主义,即认定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另一种则为怀疑主义,它把历史事实视为依附于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沃尔什提出了“配景理论”的观点,成为超越它们的第三种解决方法。
所谓“配景理论”是一种激进的“配景主义”。沃尔什将其阐释为:
历史学家为了达到我们所考虑过的那种客观理解,就不只是需要有关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局势中确实是怎样在行动的标准知识,而且还需要有关他们应该怎样行动的标准概念。他需要弄清楚的不只是他那有关事实的知识,而且还有他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观念。[30]
何兆武对其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配景理论”的要点在于:承认不同事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公约性”,即在道德和哲学观不同的历史学家那里,存在一个共同承认的历史事实;而在具有相同道德和哲学观的历史学家那里,又会有一个共同的或者客观的历史意义。最终,沃尔什的历史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成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因而获得这种客观性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学家如何获得这些基本信念的问题”[31]。沃尔什认为,其途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来自于“经验”,即混合了具有共同经验的普遍常识;另一种来自历史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沃尔什深受康德的影响。康德认为,知识有先天的成分,正是先天性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从而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不过,沃尔什也注意到康德理性中所包含的非理性的成分,因此,沃尔什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是一种主观的体会。因为,既然历史学家主要依据自己的哲学观点来研究过去,那么,他们在对历史理解的过程中,必定会一直渗透着某种主观因素。
这样一来,沃尔什的观点必然会孕育出一种丹托所批判的相对主义倾向。一方面,他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看作出于史学家自身的偏爱和喜好;另一方面,关于历史知识,沃尔什又以包含普遍真理的“客观性”为评判标准。结果,他既同意历史叙述是相对的叙述,即我们不能获得对过去的确切知识,也认可在每个对立的认识之外也存在真理。
不过,沃尔什对主观因素在历史中的强调,主要为了修正逻辑实证主义背离哲学走向技术这一倾向,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对人文主义的背弃。所以,他特意把“人性”引入了对历史的理解,主张依据时代变化的背景来理解历史。这些同丹托对“艺术世界”的时代氛围要求相一致,丹托把掌握从古至今的艺术史知识看作艺术确认的一个必要条件。另外,虽然沃尔什认为历史理解本身代表一种评价或判断,但是,他也看到康德哲学中存在过多的目的性。沃尔什指出,历史学的客观世界并不是一组事物,而是一组为每个人都同意的事实。所以历史判断中的感觉成分尽管呈现于每一个个人,却并不是个人主观的东西。[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