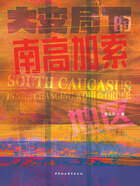
第一章 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定位
高加索地区以横亘于亚欧大陆[1]的高加索山脉为主线,北端紧靠俄罗斯文明,南端面朝伊朗高原延伸的波斯文明和安纳托利亚高地的奥斯曼文明,东端是油气资源丰富的里海,西端是兵家必争的黑海。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带动下,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在此共存。当前高加索地区由两部分组成: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北高加索,包括车臣、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赛梯等多个族群自治单元,以及三个主权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组成的南高加索[2]。地处文明的交会地,加上多样的地形特征,使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定位相对模糊复杂。本质上说,“它可以被称为地区(region),却又难以被视为地区”。[3]
在世界历史学家和地缘政治研究者眼中,南高加索地区的异域特色总是令人好奇和神往。“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4]同时,试图到这里探寻的人们又充满着因未知而产生的种种不安。迄今为止,亚欧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其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准备入侵的游牧民族促成的”。[5]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诸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蒙古种人占优势。如果着眼于地缘政治的局势,从古代到近代,“我们不难发现,高加索地区和中国都曾遭受到相同的危险,前者的危险来自波斯和罗马帝国,后者的危险来自它的北部边境”。[6]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用说,所有文明的定居民族都将游牧民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7]
东西方中间的交界地带,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在过去和今天人们的眼中也许不算十分重要的地段,而实际上,这里则如同一口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志向、不同恐惧的“沸腾大锅”——“长久以来受到压制的古老纷争和冲突,如今又被血腥地重新激起,而外部势力则在这个石油和矿产丰富的地区,争夺政治、经济或宗教的权力。历史又回到了大熔炉里,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8]今天这里是一些异邦族群和边缘国家的所在地,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高加索山脉国家;充满动荡、暴力并威胁着国际安全的地区,如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或所谓的“最佳民主实践国”,如俄罗斯和阿塞拜疆。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一系列“失败国家”和“没落国家”的聚集地;[9]因而“人们对高加索和大草原的印象十分陈旧,认为那些地区充满了暴力和犯罪”。[10]
近现代以来,南高加索地区一直是苏联(尤其是俄罗斯)连通亚欧大陆的枢纽。“从历史上来说,高加索始终紧扣俄罗斯人的心弦,索尔仁尼琴这样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对它充满恐惧和敬畏。在黑海和里海之间有一座大陆桥,欧洲在这里逐步消失于绵延600英里、高达18000英尺的群山中,那蜿蜒的山脊格外迷人,舒展而平坦的草原向北延伸”;“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感情,让他们既着迷又惶恐,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故事,也在这里打开了窗口”。[11]为了对该地区施加影响,“俄罗斯手里还有其他筹码: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波罗的海海域的强大海军基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大量讲俄语的少数民族;亲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此外,格鲁吉亚受到亲俄罗斯的分离省份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的威胁;在哈萨克斯坦的空军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覆盖范围可达中国、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塔吉克斯坦也允许俄罗斯军队巡逻其与阿富汗的边界”。[12]不同于高加索地区历史上的反帝斗争,当前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主要围绕民族自决的主题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高加索地区就已经成为苏联(或“后苏联”)空间最动荡的地域,态势延续至今。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在加强同南高加索地区的联系。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年至今为快速增长阶段。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三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 >中国—阿塞拜疆 >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中国—亚美尼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向驱动力一方面包括南高加索三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欠稳定性因素与地缘文化的强分裂性因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对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外交的难介入性因素与地缘经济的弱竞争性因素。两类驱动系统的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双方地缘关系的演变。”[13]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以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为抓手,探究中国与南高加索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地缘战略合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现有的文献中,“Eurasia”有“亚欧大陆”“亚欧地区”“欧亚大陆”和“欧亚地区”等不同表述。除引用内容以外,本书统一使用“亚欧大陆”和“欧亚地区”。
[2]除引用内容以外,本书统一使用“南高加索”。高加索山脉北面属于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因而不属于研究范围。
[3]孙超:《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
[4][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6][法]让-皮埃尔·马艾:《从埃及到高加索:探索未知的古文献世界》,阿米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97页。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8][英]彼得·霍普柯克:《新大博弈:一战中亚争霸记》,邓财英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266、416页。
[9][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Ⅱ—Ⅲ页。
[10][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
[11][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171页。
[12][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194页。
[13]巴士奇等:《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