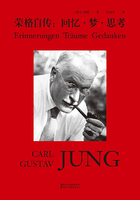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4章 大学岁月(4)
次日,我拿着碎裂的刀子去城里一个最好的刀匠那里,他用放大镜察看了裂面,摇头说道:“这把刀毫无缺陷,钢片毫发无损。有人把刀折成一片一片,比如可能插入抽屉缝里,一片一片折断。钢片好着呢。或者从高处摔到石头上,这种东西不可能爆炸。有人跟您胡说。”[10]
家母和舍妹在室内时,突然爆响把她们吓了一跳,家母的二号人格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我,我一无所知,无法解释突发之事,只能沉默。不得不承认深受影响,这令我更加恼火。桌子为何断裂,刀子为什么碎裂?假定这是巧合确实太过分了。莱茵河偏巧有朝一日往上流,极不可能,当然排除其他可能性。那会是什么呢?
几周之后,我得知某些亲戚从事显灵转桌已经良久,他们有通灵师——一个十五岁多一点的小姑娘,此中人士琢磨介绍我认识这个制造梦游状态和招魂现象的通灵师已经有一阵子了。我听说此事后,立刻想到家里的离奇现象,猜测它们与这个通灵师有关,每周六晚就定期跟她和其他感兴趣者聚会,结果是墙壁里、桌子里有说话声、敲击声。桌子不受灵媒影响而动,这很可疑。我很快查明,对条件加以限制一般会碍手碍脚,所以,只关注明显的自动敲击声,把注意力转向说话的内容。在博士论文中,我阐述了这些观察的结果[11]。我做了约十年实验之后,出现某种疲乏,而且抓住通灵师试图用欺骗的方式制造奇异现象,促使我非常遗憾地终止实验,因为从实例中学到二号人格如何形成,如何进入儿童意识,而这种意识最终如何融入自身。那个小姑娘是“早熟者”,二十六岁死于肺结核。重见时,她二十四岁,她独立、成熟的人格令人持久难忘。她死后,我从其亲属处获悉,生命中最后几个月里,个性一点一点离她而去,最终回到二岁孩童的状态,在此状态下长眠。
总之,这种重大经验抵消了我先前的人生哲学,促成自己有心理学的立场,我获悉了人类心灵的一些客观事实。但经验又使人对此无可言说,不知可以向谁告知全部真相,又不得不把值得深思之事暂且搁置。几年之后,才酝酿出了我的博士论文。
在医学临床课上,弗里德里希·冯·米勒接替了年老的伊默曼。冯·米勒其人甚得我心,我看到一个才思敏捷者如何抓住难题,表述的那些问题本身就近乎解决之道。他似乎也在我身上看出些什么,因为后来我快要毕业时,他获聘前往慕尼黑,建议我以助理医生身份随行。他的邀请几乎打动我投身内科。若不是中间出了点事,本来也极有可能到了那一步,此事打消了我对日后职业生涯的一切疑虑。
我虽然听过精神病学讲座和临床课,但当时的精神病学老师让人提不起什么精神,想起家父在疯人院,尤其是在精神病科的经历给他留下的后效,同样不容易引起我对精神病学的好感,因此缘故,具有代表性的是,准备国家考试时,精神病学教科书是最后看的,对此不抱什么期望。不过,我还记得打开克拉夫特-埃宾的书[12]时想到:好吧,现在让咱噍噍,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对他的素材有什么可说的。——讲座和临床课没给人留下丝毫印象,我想不起一个临床演示的病例,只记得无聊、厌烦。
我从前言开始,意在查明精神科医生如何介绍他们的研究对象,或者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存在的权利。不过,为了给这种狂妄做辩解,就不得不提及,当时医生圈子里,精神科地位甚低。无人真正知晓精神病学,没有一种心理学会把人作为整体来考察、并且把其病态变异也包括在考察中。院长连同病人关在同一所精神病院里,该院本身也与世隔绝,孤零零地位于城外,如同暮气沉沉的临终病院及其麻疯病人,人人不屑一顾。医生几乎与外行一样所知甚少,因此,也与门外汉感觉相同。得了精神病是毫无希望的不幸之事,这种阴影也落到精神病科上。我很快从自身经验发现,精神病科医生是奇特的人物。
我就在前言中读道:“精神病学教科书或多或少带有主观特征,原因可能在于该知识领域具有独特性、未得到完美的改进。”过了几行,作者在后面把精神病称为“个性疾病”,我突然心跳剧烈,不得不起身吸气,自觉激动不已,因为好似豁然开朗,除了精神病学,不可能有适合自己的其他目标了,兴趣的两股洪流只能在此汇合,通过拉平落差挖出河床,生物学事实与精神事实在此有共同经验领域,我曾遍寻而不得,此处总算有一处使自然与精神的冲突成为不同寻常之事。
读到克拉夫特-埃宾论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特征”时,我的激烈反应开始了,心想,那教科书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作者的主观自白,他以成见、全部的生存状态来支持他的经验的客观性,以其自身的全部人格回应“个性疾病”,我从未从临床教师那里听说过类似之事。虽然这本成问题的教科书与同类的其他书籍其实无所分别,这些不多的暗示还是给精神病学打上了一道神化之光,它们让我入迷,无可挽回。
我决心已下,告知内科教师时,可以从他脸上看出失望、惊讶之色。陌生、疏远,旧伤复发,令人痛心,但自己现在更加知道是何道理。无人想到我会对此犄角旮旯感兴趣,连我自己都不曾想到。友人吃惊、诧异,认为我是傻瓜,怎能用内科前程远大的机会换来无谓的精神病学,前者广受认可,唾手可得,如此诱人、受人妒羡。
我明了,自己显然又剑走偏锋,无人愿意或者能够支持。但我知道(没有人也没有什么能让自己怀疑这种确定性),自己的决心坚定不移,命中注定,好似两股洪流汇合,在大动荡中把人引向远方的目标,无法回头。正是“两面性合一”这种情绪高昂的感觉如同带着我在有魔力的巨浪上以头名通过毕业考试。有代表性的是,纵有百般奇迹大获成功,马脚还是接踵而至,恰恰在真正拿手的课程,也就是病理解剖中把我绊倒。
我犯了可笑的错误,觉得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一个标本似乎只包含上皮细胞,忽略了存在鹅口疮菌的那个角落。在其他课程中,我甚至凭直觉预感到会问我什么。多亏这种情况,我“旗帜飘扬、锣鼓喧天、喝彩阵阵”,绕过了一些难关,接着,在自觉最十拿九稳之处以简直怪诞的方式把自己绕了进去,自食其果,否则会以满分通过国家考试。
另一名考生与我得分相同,他独来独往,是难以捉摸、乏味得令人生疑的人物,除了“三句话不离本行”,对他根本无可奈何。他对一切报以神秘的微笑,让人想起埃伊纳城神庙山墙上浮雕人物的微笑。他身上兼具优势、劣势和尴尬意味,从未完全合乎时宜,我感到费解。他身上唯一可以确定之事,是汲汲于功名,除了医学事实和知识,似乎心无旁骛,大学毕业后没几年,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提及这件巧事,因为它是诸事件平行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我的处女作致力于精神分裂症心理学,自己人格中的先入之见在书中回应“个性疾病”:最广义上的精神病学是患病的心灵与医生号称“正常的”心灵对话,是“病”人分析诊疗者原则上同样主观的人格。我努力阐明妄想与幻觉不仅是精神病的典型症状,而且是人之常情。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的晚上,我用渴望已久的享受犒劳自己,(平生第一次)进了一回剧院。在此之前,经济状况不允许有此类铺张浪费之举。但推销古董收藏品还有些余钱,不仅使人得以看歌剧,还可以去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旅行。
比才[13]如同无垠大海的巨浪让我陶醉、倾倒,次日,火车越过边境,把人带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卡门》的旋律余音绕梁。在慕尼黑,我初次真正见到古典艺术品,它们和着比才的音乐在我身上产生一种气氛,只能推测、无法把握其深度与深刻意义。那是如沐春风、新婚宴尔的心绪,外部世界却是1900年12月1日至9日阴沉沉的一周。在斯图加特,我(最后一次)见到姑妈赖默尔-荣格博士——祖父C.G.荣格教授头婚时与维尔日妮·德拉索生的女儿,高雅迷人,蓝色双眸炯炯有神,热情奔放,丈夫是精神科医生。我觉得围绕她周身的世界充满不可触及的幻想和让人不知何处是乡关的记忆,透出正在消逝、无法回归的史前时代的余韵,与我童年时怀古癖诀别。
1900年12月10日,我在布尔克赫尔茨利岭的苏黎世大学精神病院履任助理医生。我愿意前往苏黎世,因为渐渐觉得巴塞尔过于狭隘了。在巴塞尔人眼中只有他们这座城市,只有在巴塞尔“像样”,比尔瑟河彼岸就开始“受苦”了。友人们理解不了我为何离开,估计我短期内会返回。但这不可能,因为在巴塞尔,我永远头戴牧师保尔·荣格之子和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之孙这些帽子,可谓属于某个有头脑一族,应归入特定的社会“阶层”,而自觉对此心生反感,因为不愿也不能让别人给自己定位。
在精神方面,我觉得巴塞尔的氛围难以超越,具有令人艳羡的四海一家气度,但自己觉得传统的压力过甚。前往苏黎世时,我强烈感受到了差异。苏黎世与世界的关系并非精神,而是贸易,但此处自由自在,我很看重。即使怀念丰富的文化背景,此处也感受不到千百年的沉沉暮气。如今,我仍偏爱巴塞尔,为之心痛,虽然知道它不复如初。我还记得那时有巴霍芬、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大教堂后面还有古老的牧师会礼堂和半木质结构的莱茵古桥。
我离开巴塞尔,家母难以忍受。但我知道,难免有此痛苦,她勇敢地承受了。她与舍妹共同生活,后者小我九岁,体质羸弱多病,在任何方面都与我不同,生来适合过老处女的生活,也没有结婚。但她形成出色的人格,我赞赏她的行为。她是天生的“淑女”,至死如此。她不得不接受了一次被认为危险不大的手术,但没有挺过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事先细致入微地安排了一切事宜。其实,我对她很生疏,但对她极为尊重。我更加感情用事,她虽然本性敏感,却始终镇定自若。我可以想象她身处高贵的女子修道院,正如祖父小他几岁、唯一的妹妹曾经生活在这样一所女子修道院一样。[14]
在布尔克赫尔茨利工作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处于现实中,只有意愿、自觉、义务与责任,那是进入世间寺院,服从誓愿,即只相信极有可能之事、寻常之事、平淡之事与意义贫乏之事,抛弃一切陌生之事、重要之事。徒具外表,无所掩盖,只有起始,没有延续,只有偶然性,没有关联,只有范围越来越窄的知识,贫乏才是问题,只有鼠目寸光和一望无际的墨守成规的荒漠。我有半年把自己关在院墙之内,以习惯疯人院的生活与思想意识,从头通读了整整五十册《精神病学汇刊》,以了解精神病的心理状态。我想知道,看到自毁,人的精神如何反应,因为我觉得精神病清晰地表达了所谓健全精神看见精神病时那种生物学上的反应。我觉得专业同行们与病人一样有趣,所以,随后几年里,对瑞士同行的遗传先天条件做了既秘密又富于启发性的统计,既是为了个人修身养性,也是为了理解精神病反应。
可能几乎无需提及,我的专心致志、自行幽居令同事们惊愕,他们当然不知,精神病如何让我诧异,我多么重视了解精神病的心理状态,当时绝无治疗的兴趣,但所谓正常状态的变体强烈吸引了我,因为它们提供人所企盼的可能性去加深对心灵的认识。
在这些前提下,开启了我的精神病学道路、我的主观实验,从后者可见我的客观生活。
我既无兴致亦无能力置身事外,以真正客观地观察自己的命运。我会犯自传中众所周知的错误,或者生发本该如何的错觉,或者撰写生命之歌辩词。毕竟,人是无法自评的,不管怎样,均受他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