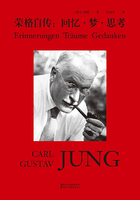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5章 疗救心灵(1)
在布尔克赫尔茨利岭的苏黎世大学精神病院的岁月是见习期,我感兴趣和研究的中心是令人焦躁不安的问题:精神病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当时尚不理解,同事中无人关心此问题。精神病学教学可谓意在不顾病人而满足于诊断、描述症状、做统计。从当时占上风的所谓临床观点来看,医生并不关心精神病人是人、是有个性者,而是用一长串诊断和症状医治第几号患者,给他“贴标签”,用诊断给他扣帽子,这个病例大半就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根本不起作用。
在此情形下,弗洛伊德帮了我的大忙,尤其是他对歇斯底里和梦的心理学做了基础探究,其见解给我指明了进一步探究并理解个案之路。弗洛伊德虽非精神病科医生,而是神经病学家,但把心理学问题带入了精神病学。
我还记得一个当时令人印象极深的病例,是一名少妇,贴着“忧郁症”的标签入院,在我的科室里。人家习以为常地给她做了细致的检查:既往症、测试、体检等等,诊断:精神分裂症,或者如当时所称“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预后诊断:很糟糕。
起初,我不敢怀疑这一诊断,当时还是年轻人、新手,不相信自己做得出不一致的诊断,不过这个病例显得奇怪,我觉得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一般的抑郁,就打算按自己的方法给这名女病人作检查。当时,我在关注诊断联想研究,就跟她做联想实验,还跟她谈论了梦境,以此方式澄清了她的过往,获悉了寻常的既往病历不曾查明的要点,可谓直接从潜意识里得到了信息,表明有悲惨黯淡的往事。
婚前,这名女士认识一个男子,一个大实业家之子,周围所有姑娘都对他感兴趣。她以为,自己长得漂亮,会中他的意,有些机会。但看来他对她不感兴趣,所以,她就嫁了别人。
五年后,一名老友来访,他们共忆往事,趁此机会,友人说:“您结婚时,对某人是打击——对您的那位X先生(大实业家之子)。”这就是契机!在此瞬间,抑郁开始了,几周后,灾难发生了:
她给孩子洗澡,先是四岁的小姑娘,然后是两岁的儿子。她生活在乡间,供水在卫生方面并非毫无瑕疵;有供饮用的纯净泉水和供洗澡、洗涤之用的受感染的河水。给小姑娘洗澡时,她看见小姑娘吮吸海绵,但未加阻止,甚至给小儿喝了一杯不洁水,当然是无心的,或者只是半清醒的,因为她已经处于开始抑郁的阴影中。
不久,过了潜伏期,小姑娘因伤寒病亡,那是她宠爱的孩子。男孩未受感染。在那一刻,抑郁急性发作,这名女士就入院了。
她是凶手,我从联想实验中看出这一事实还有她的秘密中的许多细节,我明白了,这些足以导致她抑郁,关键是心理障碍。
她的治疗情况如何呢?迄今为止,因失眠而给她服用镇痛剂,因为有自杀嫌疑,她受到监控,但此外未做什么,身体方面情况很好。
我发现自己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该开诚布公地跟她谈谈?要做大手术吗?这对我意味着难办的良知问题、空前的各种义务间的冲突,但不得不与她一起解决冲突;因为若问同事,他们可能会告诫我:“千万别跟她说这些事,您只会让她更疯狂。”依我之见,也可能起反作用。反正在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明确的真理。对一个问题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要看是否同时顾及潜意识因素。当然,我也意识到在拿什么冒险:若女病人陷入困境,那我也一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冒险采用结果极不确定的疗法。我告诉了她通过联想实验发现的一切。您可以想象,这有多难。直言不讳某人杀了人,这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事。闻听并接受此事,对女病人来说是悲剧性的。但效果是,十四天之后,她可以出院了,再未进过精神病院。
还有其他理由促使我对同事绝口不提此事,生怕他们讨论此病例,会抛出什么合情合理的疑问,虽然不能指出女病人做了什么,不过,这样一种讨论对她可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我觉得较恰当的是她复归生活正轨,在生活中抵过,她受命运的惩罚够惨了。出院时,她身背不得不承受的重负。身患抑郁、在精神病院受隔离时已经开始悔罪了,而丧女使她深受痛楚。
在许多精神病病例中,病人都有按下不表且往往无人知晓的往事。对我而言,研究了这一段个人的病史后,才开始真正的治疗,它是病人为之心力交瘁的秘密,同时包含治疗的关键。医生务必知道如何获悉此事,提问须切中此人整体,而非只是其症状。多数情况下,调查已知的材料还不够,联想实验可能开辟通道,解梦也能做到这点,或者与病人做长久、耐心、通人情的接触。
1905年,我取得精神病学大学执教资格,同年成为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医院的主治医生,任职四年之久,此后(1909年),因为工作实在令人难以招架,不得不辞职。在这些年里,我的私人诊所大到令人再也跟不上工作节奏了。但编外讲师的工作一直保留至1913年,讲授心理病理学,当然也讲授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基础以及原始人心理学,这些是主要内容。在最初几个学期中,我上大课时主要研究催眠术以及让内和弗鲁尔努瓦。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问题处于突出地位。
在上催眠术课程时,我也探询向学生介绍的病人个人病史,依旧清晰记得一个病例:
有一次来了个上年纪的妇人,约五十八岁,看起来具有宗教倾向,拄杖而行,由女仆领路,她左腿麻痹十七年,痛苦不堪。我让她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询问病史,她开始讲述并诉苦,整个病史连同杂七杂八的一切曝光了。最终,我打断她的话头,说道:“好了,没时间说这么多了,现在得给您催眠了。”刚说完,她就合上眼,进入深度昏睡状态——我未做任何催眠!我很惊讶,但不打扰她。她喋喋不休,讲述千奇百怪的梦境,都是对潜意识的深度体验,然而,我很久之后才明白这点。当时我估计是一种谵妄。但场面令人不快,在场的有二十名学生,我想给他们演示催眠!
半小时后,我再想唤醒她,她没有醒来,令人觉得不祥,一个念头袭来,我可能触动了潜在的精神病。等到我终于把她叫醒,过去了大约十分钟。这中间,还不能让学生察觉我的焦虑!女士苏醒时,晕头转向。我试图安慰她:“我是医生,一切正常。”她叫道:“可我痊愈了!”扔掉拐棍,可以行走了。我满脸通红,对学生们说道:“各位看到了,用催眠术可以达到什么效果。”但我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这是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经验之一。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那名女士确实痊愈了,欢天喜地地离去。我请她通报自己的情况,因为估计至迟二十四小时后会复发。但疼痛不再,我虽有怀疑,仍不得不接受她痊愈这一事实。
次年夏季学期第一次上大课时,她又出现了。这次,她诉说不久前才出现剧烈背痛。我认为不排除背痛与我重开大课相关,或许她在报上读到我开课的预告。我问她,何时开始疼痛,由什么引起。她却想不起在某一特定时间发生了什么,根本不知如何解释。最后,我从她嘴里问明,确实在报上见到我开大课的预告的那时那刻开始疼痛。这虽然证实了我的猜测,但仍旧不解什么会导致那次奇异的痊愈。我又对她催眠,也就是说,她又跟那次一样,自动进入昏睡状态,过后摆脱了疼痛。
大课之后,我留住她,以了解她的生活细节。情况表明,她有个弱智儿子在本院我的科室里。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氏,儿子是头婚时的独生子。当然,她希望有个聪慧成功的儿子,他年轻时就心理有疾,她深感失望。当时,我还是年轻医生,体现了她对儿子的一切愿望。因而,身为老年妇女,她将自己所抱的雄心勃勃的愿望反映到我身上。她可谓收养我为子,昭告天下奇异痊愈。
确实,我在当地有魔术师之名,要归功于她,因为这件事口口相传,连我最初的私人患者也在传。我的心理治疗实践始于一名母亲把我当成她患精神病的儿子!当然,我对她解释了其中的关联,她颇为理解地接受了一切,后来再未复发。
这是我首次真正的治疗经验,可以说是首次分析。我清晰地记得与那名老夫人的交谈,她很聪慧,很感谢我认真对待她,对她和儿子的命运表示同情,这对她很有用。
起初,在私人诊所里,我也使用催眠术,但很快放弃,因为那是在黑暗中摸索,永远不知进展或痊愈持续多久,我始终反对不明不白地工作,同样不怎么喜欢由我决定患者该做什么。我其实更在意从患者本人处了解他理所当然会向何方发展,为此,需要细致分析梦境和其他潜意识的病征。
1904—1905年,我在精神病医院设立了实验心理病理学实验室,跟一些弟子探究心理反应(即联想)。老弗朗茨·里克林是我的手下,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当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述联想实验结合心理电反射效果,而我撰写《论心理事实诊断》这篇论文。还有一些美国人,其中有卡尔·彼得森和查尔斯·里克斯赫,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专业杂志上。应该归功于联想研究的是,我后来于1909年受邀前往克拉克大学,介绍自己的工作。弗洛伊德也同时获邀,两者并无关联。我们两人均获得法学荣誉博士称号。
同样也是通过联想实验与心理电反射实验,我在美国为人所知,很快就有来自那里的众多患者。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最初病例中的一起:
一个美国同行打发一名患者来我处,诊断结论为“酒精性神经衰弱症”,估计“无法医治”。我那名美国同行预测我的治疗实验可能一事无成,为防万一,已经劝告患者找柏林的某位神经科权威问诊。患者在门诊时间就诊,我跟他略作交谈后,看出此公得的是平常的神经症,他对心理成因一无所知。我跟他做了联想实验,确诊他饱受可怕的恋母情结折磨。他出身殷实望族,有娇妻,表面上可谓无忧无虑。不过,他贪杯好饮,这是绝望之下试图自我麻醉,以忘却令人压抑的处境,当然,用此方式并未摆脱困境。
其母是大企业主,这个聪慧异常的儿子身居要职。其实,他早就不该郁闷地甘居母亲之下,但下不了决心牺牲耀眼的职位,所以依旧依附帮他获得此职位的母亲,跟她在一起或者不得不屈服于她的干涉时,就开始酗酒,以麻醉自己的情感,或者确切地说,摆脱她。其实,他却违背本能地任由富裕生活和舒适引诱,根本不愿脱离暖巢。
短期治疗之后,他停止酗酒,认为自己痊愈了。但我告诉他:“若您回归原状,我保证不了您不会又是老方一帖。”他却不信我的话,满怀信心地返回美国。
刚一置身于母亲的影响之下,他又开始酗酒了。其母在瑞士逗留时,请我去会诊。她是聪明人,却是头等权魔。我看出儿子不得不反抗什么,知道他无力抗拒,身体也有些弱不禁风,根本敌不过母亲。所以,我决定来个突然袭击,背地里给其母出具了一份鉴定书,证明他因嗜酒而无法在她的公司中长期履职,应予解职。母亲听从了此建议,儿子当然对我大为光火。
我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事通常与医生的良知不易一致,但知道,为了患者,不得不自揽责任。
他接下去的情况发展如何呢?就此与母亲分离,可以发展其个性,虽然或者恰恰因为接受了一剂猛药,还是前程辉煌。其妻非常感激我,因为丈夫不仅解除了酒瘾,而且独辟蹊径,大获成功。
我对该患者经年负疚,因为背着他出具了鉴定书,但确知只能强行使他离开母亲,这就解决了神经症。
另一病例同样难以忘怀。一名夫人前来就诊,拒绝说出名字,说名字无关紧要,她只想咨询一下。她显然属于上流社会,声称曾是医生,要向我倾诉的是忏悔,二十年前出于嫉妒而杀了人,毒死了最好的女友,因为想嫁给其夫。依她之见,若无人发现,谋杀无关紧要,想嫁女友之夫,就得除掉女友。这就是她的立场,道德顾虑不在考虑之列。
后来呢?她虽然嫁了那个男人,但他很快英年早逝。随后几年,怪事迭出,这次婚姻所生女儿一长大就力求离开母亲,早早结婚,越来越疏远,最后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她与女儿失去了任何联系。
这名女士是狂热的骑手,拥有若干坐骑,吸引她关注。一日,她发现马匹开始在她身下烦躁不安,甚至最喜爱的马也受了惊,把她摔了下来。最终,她不得不放弃骑马,现在转而与狗打交道,眷恋一只特别漂亮的狼狗,偏巧这条狗瘫痪了。因为受够了,她自觉“道德上完蛋了”。她不得不忏悔,为此目的来找我。她是杀人犯,但也杀死了自己。因为犯下此罪者就毁灭了灵魂。杀人者已经处死了自己。若有人犯罪被捕,则由法律惩罚。我们这个案例表明,若暗中犯罪,没有道德意识,而一直无人发现,仍难逃惩罚,还是会真相大白的。有时看起来连飞潜动植也“知”底细。
因为谋杀,甚至动物也与这名女士格格不入,她寂寞难耐,为排遣寂寞,把我变成知情者。她必须有并非谋杀者的知情者。她想找到一个人能够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忏悔,因为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与人的关系,但不能是专业的忏悔神父,而必须是医生。若是忏悔神父,她就会猜测,他因职务而倾听;他不会接受事实本身,而是为了做道德评判。她经历了人与动物抛弃她,深受此沉默判决的打击,再也无法忍受其他永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