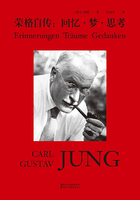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6章 疗救心灵(2)
我从未获悉她是谁,也证明不了其事符合事实,后来有时自问,她的生活可能如何会继续下去。因为她的故事当时尚未结束,或许最终导致自尽。我无法想象,她如何能在这种极端寂寞中活下去。
临床诊断很重要,因为它们提供某种定位,但对患者无所裨益。关键是患者的“病史”这个问题,因为它揭示人的背景和人的痛苦,而医生的治疗只能从那里开始,另一病例也很清晰地向我展示了这点。
那是女病区的一名老年患者、一个六十七岁的妇人,卧床四十年,入院将近五十年,但无人记得起,在此期间,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一名在院工作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对她的病史略知一二。老妇说不了话,只能进流食或半流食,用手指吃东西,多少算是把食物挖入口中,有时几乎两小时喝一杯奶。不吃东西时,就用手和胳膊做奇怪的节律性动作,不知算何性质。我对精神病可能造成的毁灭程度印象深刻,却不知如何解释。在临床课上,把她作为偏执型早发性痴呆来讲解,但这对我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丝毫没有奇怪动作的含义和成因。
此病例给我留下的印象表明了自己对当时精神病学的反应,当助理医生时,感觉根本不懂精神病学所声称之事,与上司和同事相比,自觉极其不适,他们举止老练,而我一筹莫展地在暗中摸索。我视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认识在病人内心发生之事,而自己对此尚一无所知。我入了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一行!
一天晚上,我走过科室,看见老妇做着谜一般的动作,又一次自问:为什么偏偏如此呢?就走向那位老资格的护士长,打听那名患者是否一直就是如此。她答道:“对,我前任告诉我,她以前做过鞋。”于是,我再次查阅了她以前的病历卷宗,那里写着,她做的动作像是在制鞋。以前,制鞋师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用类似的运作把线穿过皮革(如今仍可在乡村鞋匠那里见到)。患者不久后死去,兄长来出席葬礼。我问他“令妹为何得病”,他说,她爱过一名鞋匠,但他因什么原因不愿娶她,那时,她就“精神错乱了”。制鞋动作表明她至死以情人自居。
当时,我初步预感所谓“早发性痴呆”的心理起源,从那时起,全身心致力于神经症中的意义关联。
清楚记得一名女患者,借助其病史,我明白了精神病,主要是“荒唐妄想”的心理学背景,在此病例中,初次理解此前有人宣布为无意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那是芭贝特·S.,我公布了其病史[15],1908年,在苏黎世市政厅做了关于她的报告。
患者生于苏黎世老城,来自肮脏的穷街陋巷,长于寒门,姐姐是卖淫女,父亲是酒徒。她三十九岁时患有偏执型早发性痴呆,有典型的自大狂症。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住院二十年。几百名医科大学生从她那里得到精神分裂过程令人不寒而栗的印象。她是医院典型的展示对象。芭贝特全疯了,说着人们根本听不懂的事情。在艰难的工作中,我尝试理解她杂乱无章之言的内容。比如,她说:“我是罗蕾莱”,而且是因为医生试图表明态度时总是说:“我不知这什么意思。”或者她表示不满,如:“我代表苏格拉底”。我发现,这意味着:“我与苏格拉底同样遭受不公的指控。”怪话如:“我是双重综合科技学校不可替代”“我是玉米糁底上的李子蛋糕”“我是只用甜黄油做的日尔曼妮娅和赫尔维蒂娅”“那不勒斯和我得给世界提供面条”,意味着抬高身价,亦即补偿自卑感。
对芭贝特和其他类似病例的研究让我确信,许多我们以前在精神病人身上视为无意义之事根本没有看起来那么“错乱”。我不只一次体验过,此类患者背后隐藏着“本人”,应称为正常且某种程度上在旁观,偶尔也(多半通过声音或梦境)发表完全理性的评论与异议,甚至可能在躯体患病时又移至前台,让患者显得几乎正常。
有一次,要医治一名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很清楚其背后隐秘的“正常”本人。那是无法治愈、只能看护的病例。与任何医生一样,我也有痊愈无望而不得不陪伴至死的患者。那名妇人听到声音遍布全身,胸廓中间有“上帝之声”。——“我们得信赖他。”我一边告诉她,一边惊愕于自己的勇气。通常,这个声音发表的意见非常理性,借助它,我与患者和睦相处。一次,那个声音说:“上帝要考你《圣经》!”她带来一本读得旧破不堪的《圣经》,而我得每次指定她读一章,下一次考问她。此事我大约做了七年之久,每两周一次,不过,起先觉得这个角色有些奇怪,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明白,这种练习意味着什么:以此方式保持患者的注意力,使她不至于陷于潜意识让人精神崩溃的梦境。结果是,大概七年之后,以前遍布各处的声音收缩至就在身体左侧,而右侧声音全无。这一现象在左侧的强度绝非加倍,而是一如往昔。可以说,患者至少“半身痊愈”。这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没想到我们阅读《圣经》能起治疗作用。
通过对患者的研究,我明白了,受害妄想与幻觉包含的核心意义是背后有人格、生活经历、希望与愿望,若我们不解其义,原因只在我们。我初次明了,精神病中隐藏着一般人格心理学,此处也重见旧日的人类心理矛盾。即使在显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者笨头笨脑的患者身上,发生的事也比表面上更多、更合理。其实,我们在精神病人身上没有发现新事、未知之事,而是遇到自己本性的根基。当时,这种认识对我而言是强烈的情感经历。
一直令人惊奇的是,到精神病学总算专注于精神病的内容,用时何其之久。从无人自问,患者的幻想意味着什么,为何一名患者的幻想截然不同于另一名的,为何一人相信受耶稣会士迫害,另一人以为犹太人想要毒杀他,第三人认为警察在追踪他。无人认真对待幻想的内容,而是泛言“迫害妄想”,诸如此类。还觉得奇怪的是,当时的探究如今几乎遗忘殆尽。本世纪初,我就用心理治疗法治疗过精神分裂症患者,此法并非如今才发现,但仍耗时长久才开始把心理学纳入心理治疗。
我还在医院时,不得不慎重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得不小心翼翼,想要免受异想天开这种指责。精神分裂症,或者如当时所称“早发性痴呆”被视为不治之症。若精神分裂症得以成功医治,有人干脆说得的就不是精神分裂症。
1908年,弗洛伊德来苏黎世看望我,我给他演示了芭贝特这个医案。后来,他对我说:“荣格,您知道,在此患者身上所发现之事肯定很有意思。但您怎么能受得了跟这个奇丑无比的娘们儿待在一起?”——我真是有些六神无主地打量他,因为我根本从未动过这种念头。我觉得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和善的老家伙,因为她有如此美妙的妄想,说出如此有趣的事情,毕竟,在她那里,云山雾罩的胡说八道中也显露出人性。对芭贝特的治疗无甚进展,而且她已经患病太久了。但我见过其他病例,此类细究起过持续的治疗作用。
从外表看,精神病人身上只显出悲剧性的毁灭,但疏远我们的心灵鲜见生机。在那个患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患者病例中,我吃惊地体会到表象常常骗人。她十八岁,出自书香门第,十五岁遭兄弟诱骗,受同学糟蹋,十六岁起变得孤僻,躲避人群,最后,只与别人家一条看门护院的恶狗有感情联系,试图让它改弦更张。她变得越来越奇怪,十七岁进疯人院,挨了一年半。她听见有各种声音,拒绝进食,完全缄默(亦即不再说话)。我初次见到她时,她处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状态。
经过许多个星期,我才逐渐使她开口说话。克服剧烈的拘束心理之后,她说生活在月亮上,上面有人居住,但她起先只看到男人,他们马上把她带走,送到他们的妻儿逗留的一处“月下”居所。高高的月山上栖息着劫杀妇雏的吸血鬼,致使月球族有灭顶之虞,这是女性人口生活于“月下”的缘由。
我的那名女患者就决定为月球族做点什么,计划消灭吸血鬼。经过长久准备,她在为此目的而建的一座塔楼的观景平台上伺候吸血鬼,经历许多个夜晚之后,总算从远处看到它像一只乌黑的大鸟飘忽过来,她拿出献祭长刀,藏在长袍里,等着它到来。它攸地站在面前,有几副翅膀覆盖脸和全身,除了羽毛,她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她很惊讶,满怀好奇地想知道它看上去什么模样。她握着刀向它靠近,这时,翅膀霍地张开,一个仙郎立于面前,用铁掌把她抓进翼翅里,令她无法使刀。况且,她让吸血鬼的目光迷住了,根本就再也无力捅刀。它把她从地上举起,一同飞离而去。
经过此次启示之后,她又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了,拘束心理也就冒头了:我阻断了她到月球的归途,她现在再也不能离开地球了。这个世界不美好,但月球很美好,而且那里的生活富有意义。不久之后,她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复发,有一阵子躁狂不已。
两个月后出院时,又可以与她交谈了,她逐渐认识到,生活在地球上不可避免,但绝望地抗拒这种无可避免及其后果,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一次,我去她的房间探视,对她说:“这对您全无益处,您回不了月球!”她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地听着。这次,她很短时间就出院了,无可奈何地认命。
她接受了一家疗养院护理员的职位,那里的一名助理医生有些冒失地试图接近她,她报以开枪射击,幸好只导致轻伤。她居然搞到了一把手枪!她早前就随身携带上膛的手枪。在结束治疗的最后一刻,给我带来了这把枪,对我惊异的提问答道:“您要是治疗无效,我就会崩了您!”
枪击引起的激动情绪平息之后,她复返故乡,结了婚,儿女绕膝,在东部熬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未再旧疾复发。
能说什么来解释她的幻想呢?由于少女时受乱伦之苦,她觉得在世人眼中低人一等,在幻想王国中却高人一头,可谓升入神话王国;因为根据传统,乱伦是国王和众神的特权。由此却与世界完全疏离,出现精神病状况。她可谓出世,与人失去联系,远在宇宙,身处天穹,遭遇翩翩飞舞的恶魔。治疗时,她把恶魔移情到我身上,这符合规律,能够说服她过常人生活的人都有性命之虞,我当然有性命之忧。通过讲述,她在某种程度上向我出卖了恶魔,由此受制于凡人,因而能够回归现实生活,甚至结婚。
从此,我本人对精神病人的痛苦另眼相看,因为现在我也知道他们内心体验的重大事件。
常有人向我询问心理治疗法或者分析法,我无法明确回答。疗法各不相同,若医生告诉我,他严格“遵循”这种或那种“妙法”,我就怀疑疗效。文献中多谈及患者有拘束心理,几乎看起来有人想要强加于人,而灵丹验方本该自然而然在患者身上产生。——心理治疗、分析与个人一样千差万别。我尽可能给每名患者对症治疗,因为解决问题之道始终因人而异,只能有所保留地制定普遍有效的规则。只有可以逆向推理心理学真理时,它才有效。我不会考虑的解决之道,可能恰恰适合某个他人。
当然,医生必须了解所谓“妙法”,但应该谨防按部就班,只能小心应用理论前提,今天它们或许有效,明天有效的可能就是其他理论前提了,在我分析时,它们不起作用。我有意不整齐划一,就我而言,对患者只能做设身处地的理解,对每名患者都要用不同的说话方式,所以,可以听到我在一次分析时用阿德勒的口吻或者在另一次分析时用弗洛伊德的腔调说话。
关键是,我作为人面对另一人。分析意味着两名伙伴参与的对话,分析师与患者四目相对而坐,医生要说些什么,患者亦然。
心理治疗时,问题不在于“应用妙法”,所以仅研习精神病学还不够。我本人还得长期努力,直至具备心理治疗技能。1909年,我就认识到,若不理解潜伏的精神病的象征,就无法治疗,当时就开始研究神话。
若遇有文化而聪慧的患者,精神科医生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必须不拘于一切理论前提而理解患者心中真正翻腾的是什么,否则会自找麻烦,激起抵触情绪。问题确实不在于证实一种理论,而是患者理解自己与众不同。然而,若不与医生应该了解的众人观点相比,就不可能做到这点。此时,仅有医学训练还不够,因为人类心灵视野所及,远非医生诊室的眼界所能涵盖。
心灵远比躯体要错综复杂、难以企及,可谓半个世界,因为只有意识到它,它才存在。心灵因此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而精神科医生要与全世界打交道。
如今可见此问题前所未有:我们大家面临的危险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来自个人和众人的心灵。人的心理病变就是危险!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正常运转。若当今某些人惊慌失措,氢弹就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