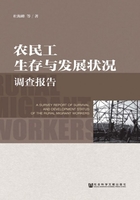
第一节 农民工生存、发展的现状
一 生计资本的现状
(一)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农民工流动行为、就业状态、社会融合状况等密切相关。本次调查从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以及健康状况等方面揭示西安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西安市农民工的总体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代农民工的教育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而接受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的比重显著提升;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东、西部地区教育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农民工父子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教育代际传承现象。参与培训有助于农民工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认证,且培训渠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业资格认证等级;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比例更高且参与培训渠道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因而比第一代农民工更能够适应就业岗位的技术要求。农民工总体健康评价状况较好,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的健康自评水平更高;来自西部的农民工健康自评水平最高,其次为东部,中部最差。
(二)社会资本
农民工进城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和社会资本再积累的过程。本次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总体社会网络规模较大,以朋友—同事—熟人关系为主、老乡次之、亲属最少;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同质性很强,普遍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少量的市民关系也是如此。同时,新生代与第一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再构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朋友—同事—熟人关系占比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拓展能力更强;与市民、政府工作人员等社会关系的交往频率更高;未成年时期的随迁经历对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此外,通过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可以发现,农民工的总体社会网络在性别上的差异呈扩大之势,地域差异则逐步减小,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能力更弱。
二 生存与发展的现状
(一)就业状况
在城市就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原因。本次调查发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正规性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而就业职位相似,但自雇就业的比例只有第一代的1/2,工资水平低于第一代农民工。从流动模式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表现出有务农经历的比例低、流入西安前在其他城市的务工经历少,以及在西安工作变换频率高的“两低一高”特点。如果以收入作为就业效果的衡量标准,可以发现丰富的跨地域流动和工作经历有利于促进收入水平提高,而在西安更换工作频率越高,收入水平则会相应降低。此外,未成年期的随迁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和职业地位。
(二)婚姻与家庭
农民工的流动不仅会影响其婚姻行为,也会对农民工两性间的经济权利结构分配产生重大冲击。本次调查着重考查了农民工的婚姻行为、夫妻流动模式和夫妻间经济结构、家庭权利分配格局及隐藏在这些权利背后的性别角色意识、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力图全方位展示农民工的婚姻与家庭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在26岁之前完婚,通婚圈以本县内为主,“夫长妻幼”“夫妻教育相同”是农民工夫妻婚姻匹配的主流模式,“夫妻共同流动”是当前农民工家庭流动的主要方式;外出打工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行为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农民工婚姻行为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农民工。夫妻双方共同决策是农民工家庭事务决策的主要形式,家庭权利的性别格局很明显,表现为妻子的权利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日常事务决策,丈夫的权利空间则以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为主;个人拥有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大小随其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加或减少而发生线性变动,夫妻经济地位平等的家庭中“夫妻平权”的比例最高。尽管“夫妻共同流动”的外出打工模式尚未扭转夫妻间经济权利地位的不平等局面,依然以“男性主导”为主;但女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有利于降低其在家庭中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激发她们要求平等的意识,促进夫妻间经济权利地位从传统“男高女低”向“男女平等”转变。
(三)融合与信任
社会融合问题已经成为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信任则是社会融合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会融合整体水平仍然不够高,其中文化融合水平略高于心理融合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合状况明显优于第一代;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而有过社会歧视经历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较差;农民工与市民交往的范围越广,其社会融合状况越好;留守随迁经历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社会信任感总体不高,特殊信任感高于一般信任感,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已经趋向成熟,而新生代农民工还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男性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普遍高于女性;来自省内农民工的特殊信任感更高,而省外农民工的一般信任感更高;社区互助水平低的农民工的特殊信任感更高,而一般信任感则会较低;参与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的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感反而更低;有随迁经历的农民工的特殊信任感最高,一般信任感最低,而有留守经历的农民工的一般信任感最高。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偏低,呈现明显的年龄模式,第一代、女性和来自省外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更高;农民工的特殊信任感越低、一般信任感越高,其政府信任感越高;权威价值观、外部效能感、公民权意识强的农民工的政府信任感高,而内部效能感高的农民工信任感低;有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的政府信任感总体上低于没有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的政策满意度越高,政府信任感越高。
(四)失范与安全
农民工群体日益增多的失范行为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自身的安全状况是城市安全和个人福利的主要内容。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遭受权益侵害相比,一般冲突问题更容易引发农民工的失范行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尽管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的比例更高,但同时,采取失范行为的比例也更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个人安全状况不太理想,遭受安全侵害的事件普遍发生,特别是人身财产安全侵害。在个人安全感方面,男性农民工安全感普遍高于女性;同时存在显著的安全感年龄模式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的安全感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安全感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普遍存在的歧视和所处社区较差的安全状况是农民工个人安全感偏低的主要原因。
(五)政治参与
在城市中政治权利的缺失和损害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参与是农民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偏好基本一致,人大选举、向政府反映问题和参加座谈会是其政治参与的最主要选择;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农民工均普遍表现出低参与水平、高参与意愿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更大,表现出更高的非制度化、对抗性政治参与的倾向;女性农民工尤其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参与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政治心理的现代化和城市组织有助于农民工政治参与;而农民工群体中收入水平的差异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未成年时期的留守、随迁经历则可能带来其群体内部政治参与行为和意识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