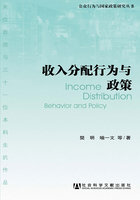
第三节 晚清时期收入分配思想
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将清政府紧闭的大门撞开,导致中国无可奈何地走向开放。西方的经济掠夺和武力征服使清政府背负巨额债款,导致清政府税赋增加,人民负担沉重。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传入,也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与繁荣。面对如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主题。有人主张捍卫传统,有人则主张革新变法,向西方学习。这一时期的争论也涉及收入分配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启发当今。
一 洋务派的收入分配思想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有过多次战争,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基本上都以惨败而告终。由此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的工业产品、生产技术以及企业经营方式传到中国,让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科技和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提出向西方学习。在此背景下,洋务运动兴起,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派不仅强调发展民族工商业,对于收入分配也形成一定的看法。
魏源(1794~1857年),名远达,字默深,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魏源的收入分配思想也充满了革新的精神。
首先,他对传统的“崇俭抑奢”的思想进行了发展。他反对单纯地抑制富人消费,认为富人适当的消费可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与收入的机会,可以更平均地促进社会的进步。“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娱乐,皆巨室与贫民通工易事,泽及三族……如上并禁之……彼贫民安所仰给乎?”(《默觚下·治篇十四》)这就是说,富人的消费可导致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再分配,进而让社会收入的分配变得更加均衡。所以说,他并不主张人为地将财富进行再分配,而是主张通过富人多消费的方法使财富自然而然地在不同阶层之间进行分配。其次,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上,他坚持传统的富民思想,认为国家必须藏富于民,由民众而非官府来掌握大多数财富。只有这样,人民才不会在巨大灾害或战争中因为受到损失而无法生存,整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维持正常的运转。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早年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出使西洋,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有着先进的维新思想。他是晚清时期要求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推动者,其“工体商用”要求中国也走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模式,推动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则尚居商之先。”(《振工百说》)薛福成鼓励发展机械制造业,将国内转型为大机器生产。一方面,大机器的运作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建立近代企业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以解决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就业问题。
薛福成的分配理念从宏观上讲,是改变生产方式从而改变分配方式。近代经济发展为社会的收入分配提供了新的方式,以前靠天吃饭的百姓现在也可以得到充足稳定的收入,分配主体从农民、地主延伸到工人、资本家,分配内容从土地、粮食发展到工资、利润,分配关系从官与民、民与民扩展到官与商、商与民。从微观上讲,从官营到官督民办再到民营企业,他将政府所占的资源优势、政治优势逐渐下放到民间,令普通商民在大机器生产中也能有所作为。这实质上是将政府的一部分经营利润分配给了民众,改善了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分配状况。在这一点,郑观应则有着更多的呼吁。
郑观应(18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出版了震惊朝野的《盛世危言》。“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尊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盛世危言·商务二》)这就是说,将政府的经营贸易分与民商,减少政府的所得利润,增加民众所能创造的利润。这一观点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国家为主人的工商企业交由少数个人来管理都是有所缺失的,企业的所有权和所得利润不属于个人,个人必不能尽职尽责,更甚者偷工减料、贪污腐败也大有为之,这样国家所得分配不能更多,而商民所得分配只能愈少。若放手将贸易交给民间和市场,政府做好守夜人的工作,分配必会向越来公平的方向发展。
二 严复的收入分配思想
严复(1854~1921年),原名传初、宗光,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近代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其他维新思想家共同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主张。次年翻译出版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之后又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严复有以下主张。
首先,严复反对绝对平均的收入分配,认为这样做会挫伤贤者的生产积极性,影响效率,最终只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在《原富》的按语中说道:“设强而同之,使民之收效取酬,贤不肖无以异,甚或不肖者道长,贤者道消,则江河日下,灭种亡国,在旦暮间耳。”“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及计学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发挥自己的潜质,获得收入。但同时他也认识到,完全放任由市场来处理所有的经济问题是不合适的。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为西方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西方的收入分配差距却非常巨大,社会并不稳定。“是以国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所以,国家也应当适当的控制收入差距,最终做到一种“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的状态(《原强》),这样一来,就算是太平盛世了。
其次,严复还十分重视财政的作用。他在税收上主张“赋无厚薄唯其宜”。在他看来税收没有绝对的标准,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教民之财”“养民之才”等重点领域要取消纳税,只要是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赋税制度便是好的。其次,他很赞同斯密的财富再分配思想,这在他著写《原富》的按语中也曾提及,“民生而有群,徒群不足以相保,于是乎有国家君吏之设。国家君吏者,所以治此群也。治人者势不能以自养,于是乎养于治于人之人。而凡一群所资之公利……皆必待财力而后举。故曰:斌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他认为,拿国家的税收来为国民建设教育、交通、国防等基础设施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国民将收入的一部分交予政府,实质上是要求政府用此进行公共维护,若政府能将其好好利用进行公共建设,那国民就相当获取了物质形式的分配。这种思想对于反对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横征暴敛,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严复是把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探讨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启迪十分深远。他的收入分配思想,虽大多借鉴西方,却给国民开辟了一个新思路。
三 康有为的收入分配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的著作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而他所提倡的分配理念主要在《大同书》中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要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首先要做到生产资料公有。他对资本主义“百事万业,皆祖竞争”的经济制度十分厌恶,认为这是西方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他主张,“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以公”(《大同书》)。也就是说,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切工业、农业、商业、银行、交通均由政府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不论生产者还是领导者,都是领工资的工人。这就意味着,将国内所生产的一切财产都交予国家分配。政府要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有计划的分配,要使“工人之作器适与生人之用器相等”“举全地所出之百谷、花果、草木、牧畜、渔产、矿产替适足以应全地人数之所需”。
与此同时,他并不反对私人企业的存在。土地是公有的,但是可以租给个人耕种。矿产是公有的,但是可以承包给个人开发。这一切私有的前提则是由政府计划生产与流通,这样才能保证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至于劳动者工资高低,则由个人才能所决定。他反对工资差距较大,但支持大额货币奖金奖励仁者智者。这样既保证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温饱无忧,又能令社会中贤能之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使社会产生尚贤尚能的良好风气。这样的分配制度既能保证公平,也不耽误效率。此外,在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上,他主张建立公共食堂、公共娱乐场等公共基础设施。他还主张大力建设教育、医疗、幼儿园、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障机构,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康有为的《大同书》不仅继承发展了传统儒家的大同思想,也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平等、民主等精华。虽然此书真正出版已是康有为身后之事,但他所主张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认为是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
四 梁启超的收入分配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他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是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他的分配思想也有着深刻的革新意味。
鉴于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以及西方在经济、思想、宗教等对中国的大肆入侵,梁启超提出了改革赋税制度,并发表了《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等文,对税制进行探讨。首先,他认为应当对土地赋税进行改革。因为当时土地赋税种类过多、数额太大,导致农民承受了巨大的负担。而这样又不利于生活和农业生产,所以他认为应当适当减少田赋,以减轻农民压力。其次,他认为关于土地赋税的处理还应当区分不同的用途。对于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应当区分对待。对于城市建设过程中使用的土地,因为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增值,所以应当收取比较大的税额,以维持公平。此外除了土地,他还认为,国家应当适当地调整税种。因为经济的发展,很多税种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求,如厘金、常关税、茶税等。而对于市场已经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现有税制又缺乏配套的管理方法,如印花税、遗产税、所得税等。所以他提出改革税制。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财政适应经济新变化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以更好地调节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
梁启超还对所谓“生利与分利”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受亚当·斯密的影响,他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成“生利者”与“分利者”。“一曰直接以生利者,若农若工之类是也;二曰间接生利者,若商人若军人若政治家若教育家之类是也。”(《新民说·论生利分利》)生利者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分利者则是寄生在生利者阶层之上的一个阶层,他们凭借各种因素不劳而获,从生利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中分割一部分用于自己的消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否取决于两个阶层人数的对比与利益划分的比重。“申而言之,则国之兴衰,一视其是资本总劳力有所复无所复而已。”(《新民说·论生利分利》)
一种正确的收入分配方法就应当是让生利者多得、分利者少得,这样才能更加调动生利者的积极性。但是,经过他的测算,中国的分利者多于生利者,正如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穷国一样。所以,中国的改革在他看来也是迫在眉睫。
五 太平天国的收入分配思想
1853年农民起义军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为人民描绘了一个天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
《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土地的平均分配有着十分详尽的规定:把每亩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好坏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以此使农民拥有同等的劳动资料,实现平均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除此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生活资料的分配做出了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而国库所收的剩余农副产品,一部分由国家统一调拨,以丰贩荒;另一部分则由两司马掌握,“存其钱谷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谷及典出入”。
《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农民要求朴素算术平均的财富分配方式。其财产公有制的基本改革路线是从土地到棉粮钱,都要交由政府统一管理分配。这又是完全抛弃市场而将公有财产集中于一人之手的例子,由此我们便可以肯定太平天国是必然走向灭亡的。任何非市场化的经济政策都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
晚清社会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国门洞开让国人看到外部世界,其内资本主义经济正逐渐兴起,整个社会要求改革渐成风气。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先行者们逐渐认识到为救亡图存,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借鉴西方的制度,也要避免西方已经出现的贫富悬殊,所提出的收入分配思想主张基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许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其革新性仍对当时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也存在逆时代潮流的太平天国平均主义分配思想,但因其在实践上无实际的可操作性,故并未产生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