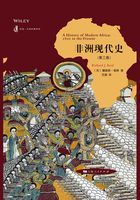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战争、变革与祖鲁冲击
在现代文学中,在欧洲的大众想象中,在学术著作中,还有晚近的电视和电影,大量谈论祖鲁的兴起,尤其是他们最著名的领袖——某种意义上的创建之父——沙卡(Shaka)。[6]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的祖鲁历史中,有许多东西证明这种狂热的着迷,在沙卡的个人历史中也有许多东西支持关于他政治和军事天赋的种种说法;然而,记住恩戈尼于18世纪开始变革时所达到的程度是很重要的,当时祖鲁不过是一个广阔得多的政治变革进程中的小小部分(是这个进程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沙卡以及在许多方面都由他个人创造的祖鲁国,采纳了在人丁年龄管理、战争形式、武器装备和政治层面上的那些变革,使用这些起到了极好的效果,但它们本质上并非祖鲁本身的创新。认识到另外一点也很重要:19世纪早期南部非洲内陆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直在引发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席卷内陆的一系列战争——它们被称作“姆费坎尼”(mfecane),这出自科萨语(Xhosa),意思是赤贫和饥饿;或索托语(Sotho)中称为“迪法盖”(difagane),意思是“摧毁”——及其后果都被欧洲人有意夸大了,为的是论证殖民主义的合理性,论证后来的种族隔离国家的合理性。[7]然而,历史学界的共识认为,最终导致祖鲁出现的“姆费坎尼”,是在南非南端低地的马兹斯瓦、恩德万德韦和恩格瓦尼这些恩戈尼国家中出现的,事实上形成了争夺有限资源的长期战争状态,对各地较小酋长国的吞并,以及中央集权和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王权。[8]
大约是在1816年至1819年间,“姆费坎尼”达到高点,在这一时期,索布胡扎的恩格瓦尼被朝北驱逐,在接下来的恩德万德韦与马兹斯瓦的冲突中,当马兹斯瓦的领袖丁格斯瓦约死后,恩德万德韦看来占了上风。不过,丁格斯瓦约军队中的一位指挥官沙卡——他当时指挥小小的祖鲁酋长国,崛起并掌握了控制权,在一系列与恩德万德韦的遭遇战中击败了他们,几个其他的恩戈尼部族于是朝北逃出了这一地区。这些难民蹂躏了整个中南和东部非洲:恩德贝勒的领袖姆兹利卡兹越过林波波河,定居于现在的津巴布韦一带;其他人则穿过赞比西河,进入现在的马拉维地区,在这里他们在文化和军事组织上对切瓦族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族群也是朝北流窜,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进入坦桑尼亚,抵达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边,一路上留下了相当的动荡和破坏。[9]不管走到哪里,这些群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经常成为一个地区活跃的奴隶掠抢者,与早已定居在林波波河与大湖地区之间的那些民族发生冲突。迁移的恩戈尼族群,为逃避祖鲁的胜利也朝更南边的地方去,在“姆费坎尼”之后的数十年中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国家建构和战争进行的新模式。还有一些国家和族群为保护自己、抵挡祖鲁威胁的需要而兴起,尤其是穆苏苏领导的索托,他在现在的莱索托一带建立了一个山区要塞,吸引了一些难民群体。他的外交才能也广为人知,通过与邻近首领们的联姻,一直保持着自己国家的独立;他还善于在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制造不和,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看到。[10]
英文版原书页码:74-75

19世纪的南部非洲。引自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年),第354页,1976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
祖鲁的影响的确与他们的实际人数完全不相称,至少开始时是这样,事实上到1819年时,沙卡已经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者而确立起来,这个国家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支配性力量,直到1879年被英国人击败并毁灭。然而,即使他们被英国人征服后,祖鲁仍然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意味,在殖民时代及其之后都是如此。祖鲁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政治和军事变革的持续以及强化,这场变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它涉及政治组织的一种新模式。祖鲁国比这一地区此前的任何国家都要大,它超越了血族关系,发展出一种建立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之上的新的身份认同,以及疆域的统一。这是一个同时具有高度凝聚性和进犯扩张性的社会,沙卡常派出他的部队去掠夺周围的民族以获取贡品,或者是干脆把它们完全吞并入自己的王国。那些新近征服的地区被分配给沙卡直接任命的首领,符合条件的青年被征募;那些持续抵抗的族群或者是被消灭,或者是被迫迁到祖鲁军队势力范围以外。祖鲁人以恩德万德韦和马兹斯瓦军队业已建立的东西为基础,进行军事创新,其中包括常备军“阿玛布托”(amabutho)的建立,强调纪律和严厉训练,使用短矛刺杀——这比投掷长矛更有效果,在袭击时注重速度和突然性,以及“公牛之角”战术的发展——也就是从侧翼来包围和消灭敌人。这套系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沙卡对作战部队行使直接控制。这些部队也有经济效用,其中的年轻人要放养畜群,猎象取牙,而女性则为国家种地。这种对国家服务的编制村庄,在祖鲁王国各地都建立起来,只有当某个年龄段的成员到了适婚年龄,这个编制村庄才会裁减,让原来的武士们到别处定居,去种自己的地。[11]总之,祖鲁这套编制系统起到了反复灌输一个更大“国家”的身份认同的作用,侵蚀着原来的地区和血亲忠诚,推进了一种显著的祖鲁意识,它的基础就是对一个以沙卡本人为中心的强大王权的崇拜,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沙卡显然是一位独裁统治者,他身上被添加了许多残忍罪行,死后就如活着时一样。1828年,由于他异母弟弟丁加恩的教唆——或者是亲手所为,他被暗杀,丁加恩继位。通常的看法认为,沙卡在后期已变得极不稳定,所行使的统治特点就是周期性的大规模屠杀,权力都集中于他手中,只有靠暗杀才能使他让位。[12]
英文版原书页码:76
对于“姆费坎尼”和祖鲁国的崛起,一直有各种解说。为什么“姆费坎尼”会在那时候发生,为什么它是那种形式,这些问题都争论不休;还有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这个地区被暴力冲突吞没的说法在何种程度上只是种族主义者的一个虚构,以论证后来白人统治的合理性,也是看法不一。有些评论者认为,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战争模式,以及祖鲁国自身的崛起,都可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非洲人是在模仿欧洲人的指挥模式和战斗模式。这种种族主义的假设显示了一种根本上的怀疑,认为非洲人自身做不到政治层面上的那种扩展,做不到军事组织上的那种变革,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显然没有事实说明像兹韦迪、丁格斯瓦约和沙卡这样的领袖只是受到了欧洲模式的影响和启发,哪怕海岸一带的葡萄牙人的确提供了这种模式。相反,更为严肃的解释旨在说明对土地和贸易的竞争才是战争升级的驱动力。人口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土地短缺导致了对牧场和牲畜的竞争,这本身又因干旱气候而激化。与此同时,尽管贸易的作用不应被夸大——不同于尼亚姆韦齐人或约鲁巴人的情况,它作为一种动力在恩戈尼人中很可能没那么重要,但认识不到象牙和奴隶贸易所起的作用,就无法充分理解“姆费坎尼”,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越到18世纪后期,象牙和奴隶贸易的作用就越重要。非洲其他部分在19世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样,哪里有全球贸易的增长,哪里就有垄断它的企图。最后,罕见天才人物的作用——最著名的就是沙卡本人——是必须被承认的,而且当代欧洲人显然想把很多东西都归于他本身;[13]然而,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发生的事情,必须放在一个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中才能得到理解。沙卡的个人作用并非不重要,卓越、善于抓住机会,最终极不稳定,他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创建了一个国家和一种身份认同——在此之前它们不存在;然而,那些围绕他而衍生的故事——他如何害怕老迈、他对母亲的极端依恋、他的性取向(他从未结婚),都常常是相当不可靠的,是为了娱乐他死后几十年中那些围坐在露营篝火旁的欧洲人。[14]
英文版原书页码:77
与在他死后出现的那些问题对比来看,沙卡的成就更显得戏剧性,他的继任者丁加恩(1828—1840)和姆蓬迪(1840—1872)必须去与已经极大改变了的政治环境斗争。丁加恩缺乏异母兄长的那种军事敏锐和领导天赋,但也必须考虑到白人定居地业已推进,到30年代结束时,它已是祖鲁面临的严峻挑战了。随着白人“移民先驱”从开普殖民地的方向推进至内陆高原,他们的力量和自信都在增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非洲天才、祖鲁国王沙卡的画像,约1816—1828年。
大英图书馆/HIP/Topfoto。来源:大英博物馆许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