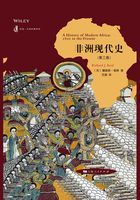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开普殖民政策:白人殖民地与“土著问题”
英文版原书页码:78
南非的现代历史,其特点就是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冲突,后者的霸权在20世纪的许多年中都导致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的曲解。南非历史的“白人”版本说那些讲班图语、刀耕火种的农人只是到17世纪才来到现在的南非这片地区,与第一批荷兰定居者抵达此处几乎是同时。所以,根据这种说法,欧洲人遇到的是一片“空白土地”,只有一些科伊桑人居住,他们被轻蔑地称为“丛林人”和“霍屯督人”(Hottetots)。[15]这种“空白土地”的理论在历史上不正确,但在政治上却有利,后来就为人数少的白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理由,来宣布对这一大片区域的权利。事实上,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当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到来时,一系列的非洲国家和社会已经居住在这一区域,从纳米比亚的奥万博和赫雷罗以及居住在纳米比亚南部和开普西南部的科伊桑人,一直到中部高原的索托和茨瓦纳,乃至东南部的恩戈尼族。
白人在南部非洲定居的时间是17世纪中期,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塔布尔湾(Table Bay)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补给站。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后来所称的“布尔人”(Boers,荷兰语中的“农夫”)或“南非白人”(Afrikaners)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语言和文化。边疆布尔人更是一些强硬、头脑独立的加尔文教徒,后来发展出一种尖锐的反英国倾向,他们开始把开普敦周围一带——也就是后来的开普殖民地视为属于他们的,这种宣称靠一种特别的人种和宗教意识形态来支持。他们起先与科伊桑人贸易,换取食物和淡水,但不久就与非洲人发生了冲突,主要是要控制放牧土地,布尔人要根据“征服权利”的原则来占有它。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时,这样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更多的布尔人“移民先驱”进入内陆去寻找优良牧场,尤其是到东边去寻找。科伊桑人面对布尔人的军事优势和带来的那些疾病(尤其是过路船只带来的天花),或是变成了猎人兼抢掠者去袭击布尔人的农场,或是朝北撤退,逃离布尔人前进的线路,他们在北边重建了自己的社会,找回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这种政策尤其得到那些科伊桑人与欧洲人通婚后代的欢迎。当然,许多科伊桑人接受了欧洲族群中的奴隶地位,为布尔人当牧人、猎人和仆人,他们是殖民地社会中一个很大部分,但从来没有相应地得到过公民权利。[16]
尽管开始时荷兰开普殖民地的种族间关系较为灵活正常,但随着时间推移,种族态度就变得强硬了,尤其是到了18世纪。当时可能还没有一种僵硬的种族划分体系,但已经有了依据肤色而来的强烈的阶层感和相对的特权。大体而言,越来越苛刻的种族主义因欧洲人与非洲人在边疆扩张争夺资源上的冲突而导出,在殖民地内,人的地位也越来越与他的肤色和工作相关。最赤裸裸的是,奴隶地位依人的肤色来区分:有着“混合”父母的奴隶通常是技术劳工,尤其可以做一些管理工作;而那些最差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就由非洲人或者是来自印尼的奴隶来做;体力活由最底层的奴隶来做,通常是非洲人,从18世纪后期以来就这样严格划分。奴隶制支撑着开普殖民地社会和经济,而奴隶本身也越来越以种族划分,这就是南非国家和社会未来形态的一种预示。[17]
英文版原书页码:79
开普殖民地在1795年之前由荷兰人控制,但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的这一年被英国夺取,1806年后一直由英国控制。19世纪20年代以后,荷兰血统的殖民者中出现了第一批英国移民,两个白人族群中的紧张关系很快激化,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语言和殖民地未来的看法上都有明显的分歧。布尔人对殖民地中央权威的敌意一直在增大。1795年,在荷兰控制的最后几周内,就曾出现过一次短暂的荷兰人造反,后来在1799年又出现了一次,被英国人镇压下去。这两次造反的原因都是认为开普当局未能关注荷兰人对土地和安全的要求,他们有一种被出卖和被疏离的感觉,对于这一地区的未来而言这是一种预兆。显然,大体而言,两个白人族群之间紧张关系的激化是由英国行使了管理权而来,布尔人对此的怨恨为这大片地区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殖民地东部边疆的扩张和定居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白人已经逐渐朝东推进,对科萨人形成了压迫。有着紧密社会结构和大片牧群的科萨人,尽管原来与白人有过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现在变成了他们东进的一种障碍。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布尔人进入祖费尔德(Zuurveld)这片重要的科萨人牧场,冲突就变得尤其激烈了。不过,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种零星的所谓“边疆战争”,并没有导致白人的长久定居。[18]
随着“姆费坎尼”在内陆腹地蔓延,布尔人定居者与新的英国管理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政府官员中的布尔人被英国官员替换,英语进入教育和法律体系之中,在非洲人劳动力的问题上也出现了进一步的紧张。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相对宽松,非洲劳工有一定的基本权利,比如受法律合同约束的权利,当雇主违背合同时有权与他打官司,这让绝大多数布尔人惊骇。他们长期来视非洲人与畜力差不多,尤其是那些勉强能够生存的贫穷的布尔人社区,它们更需要这样使用非洲人。最坏时,非洲人被视为必须除掉的害虫,至少也要赶到看不见的地方去,许多科伊桑人就这样被对待。开普的英国人只是一些闯入者,一些“城里人”,他们对待“土人”的那种“教化”和“宽大”的做法,与边疆生活的真实情况完全扯不上。而且,英国人引入了一种私人拥有土地的制度,替代了原来的租借农场制度,布尔人原来是靠从政府贷款来占有土地,在新制度下买得起土地的人不多,这种新制度是那些麻木不仁的,讲英语的大都市管理者们制定出来的。
英文版原书页码:80
除了在官方层面对业已存在的做法进行干预之外,英国传教士也越来越把开普作为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地方。由于同情被压迫的科伊桑人,他们鼓励这些农人在传教士驻地一带种地,在法庭上帮他们打官司,英国传教士与布尔人社区就进一步疏远了。在推进自己的非洲使命时,传教士们还对政府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劳动力问题上。对布尔人的感受和经济要求的最大打击,或许是1834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管理当局废除奴隶制。对于那些在殖民地经济生存末端挣扎的贫穷白人农民来说,这更是灾难,他们拿不出有竞争力的工资来雇用自由劳动力。[19]“穷白人”这个问题在随后数十年中成为塑造南非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时,许多布尔人开始考虑朝北移居逃到殖民地边疆以外的可能性,当时称为“进入非洲”,远离英国压迫。那些住在东开普的人一直在游说政府支持这样做,把科萨人从这一区域清除,为布尔人定居腾出地方。然而,尽管英国人表现得愿意在殖民地之内对布尔人的事情进行干预,但他们并不愿意帮助那些处在殖民地边缘,抱怨土地短缺,受到科萨人袭击的布尔人。政府拒绝卷入昂贵的战争,或者是支持同样麻烦的管理范围扩展——如果战争胜利的话,必然出现这种管理范围扩展。对土地的渴望,驱使布尔人考虑穿越边疆进入内陆,以寻找牧场和政治自由。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和后期,数千个布尔人家庭开始北上,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作“大跋涉”。它成了神话传奇的材料,一个团结一致、富有凝聚力的迁移理想,一次“出埃及”,它成为后来出现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一块基石,在歌中、诗中和传诵的英雄主义中被咏唱。[20]事实上,它只是一些小型的、并无联系的移动,数百个不相干的群体在行进方向上没有多大一致,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只是对英国人的憎恶和对土地的渴望。30年代和40年代的白人移民先驱们,绝大部分来自东开普,他们的迁移导致了白人在南非内陆的永久定居。然而,这些“布尔共和国”的位置却由非洲人口在局部地区的分布情况而决定。比如,许多早期的布尔人定居点都选择了“姆费坎尼”的突变造成的暂时无人区。在其他地区,出现了布尔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合作,例如在瓦尔河中部地区,罗兰人就谨慎地欢迎布尔人,将他们视作武装精良的同盟来对抗恩德贝勒人。正是1837年一场布尔人与罗兰人对恩德贝勒的联合袭击,迫使恩德贝勒人撤出了林波波河北部。布尔人在瓦尔河中部一带定居下来,随着他们信心和力量的增长,他们就能够从罗兰人和茨瓦纳人那里榨取劳动力和贡品了。[21]
在北边和东边,一些小小的移民先驱群体紧张地生活在强大得多的非洲国家和社会之间,尤其是斯威士人,当然还有祖鲁人,他们的存在对于获得这一地区令人向往的牧场是一个障碍。布尔人与祖鲁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尽管丁加恩开始时试图让白人新来者相信他们会达成妥协,和平相处。丁加恩是否真想这样做已经无从知晓了,但他1838年的做法却是相反,他对布尔人发动了一场袭击,大量布尔人被杀掉,但丁加恩也发现了——如同许多非洲统治者在他之后也会发现的那样——这些白人携带的新式武器的威力。白人重新集结,彻底击败了祖鲁人,这就是所谓的“血河之战”——血是非洲人的。[22]不过,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要过分估计处在祖鲁王国边缘的小小布尔人“共和国”的力量。布尔人表现出对祖鲁人不情愿的尊重以避免与祖鲁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他们朝南迁移了一些,建立了纳塔尔“共和国”。祖鲁人自己也因开始时与布尔人的冲突受到震荡,内部也发生了战乱,不幸的丁加恩死去,由姆蓬迪继任。然而,在姆蓬迪的统治下,祖鲁王国得到恢复,一直是白人想支配这一地区的一个重大障碍,直至19世纪后期。
英文版原书页码: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