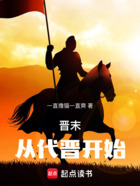
第8章 事在人为,可疑人员
北府军的建立有很大特殊性。
二十三年前,为抵御已一统北方的前秦,朝廷才命谢玄主导,招募京口等地流民、兵众,建立的北府军。
刘牢之、孙无终等人便是那时加入。
谢琰清楚的知道。
要想组建独立军队,必须朝廷允许,不然就是乱臣贼子,与孙恩无异!
现在北边的拓跋珪、姚兴、慕容盛等人这些年打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忌南边。
大晋现在并无灭国威胁。
不管是司马元显,还是刘牢之,亦或是桓玄,甚至各世家大族,绝对不会同意,第二个类似北府军的独立军事力量出现。
一个北府军,已经是各方能容忍的极限。
“为何不能?孙恩祸乱三吴,各地流民甚多,您可在各州郡县,广招乡勇、流民,挂于军中名下,日夜训练。这部分人,由我谢氏亲信掌控。”
“而后,将孙恩逼至丹徒附近,大胜刘牢之,我们再去救援,赶走孙恩。顺势陈情贼寇势众,如跗骨之蛆,提出组建南府军抵御。”
“若司马元显等人同意,一切皆好,南府军名正言顺。”
“即便不同意,甚至朝廷忌惮您。”
“介时您携击退贼寇之功,又有亲信兵众,司马元显不敢轻易夺您军权。”
“我们便在三吴继续壮大自身,招募流民,元显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时间一长,您不是北府,胜似北府!”
谢肇、谢峻听得目瞪口呆。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三弟居然如此胆大妄为。
借讨贼之名,招流民训练,由谢氏亲信掌控。
这他娘的是借鸡下蛋,养私兵啊!
后面还要驱赶贼寇去丹徒...
这...这...
两兄弟已经不知道如何评价了,狗胆包天都是夸奖他。
“走祖逖、郗鉴的路子?”
谢琰沉声问道。
谢混含笑,颔首以对。
不过,祖逖是为了收服失地,才招流民组成北伐军团。
郗鉴作为流民帅,也曾帮朝廷抗击王敦,进入中枢后,还调解王、庾关系,维护东晋统治。
而他。
可不是为了北伐。
也不是要帮朝廷抗击桓玄。
“如何保证孙恩会去袭击丹徒?”
“又如何保证刘牢之会败?”
“甚至我们赶去后,一定能战而胜之?”
谢琰一连三问抛出,明显很是意动,也将谢混的话听了进去。
忠君?
晋朝根子上,就不存在这个词。
于这个时代的士族子弟而言,家族兴盛,放在首位。
其他的,都往后稍稍。
谢肇、谢峻满脸惊骇。
父亲居然没有驳斥三弟,甚至还在跟他讨论。
这可是欺君罔上之罪!
“父亲,这些我都不能保证。但有一句话,相信您一定听过。”
“什么话?”
“事在人为!”
...
翌日。
谢肇一早便走了,是被谢琰赶回京师的。
用谢琰的话讲,早一日回去,就早一日做官,也能早一日为谢氏做贡献。
但严格嘱咐他,千万不能进司马元显的西府,只能在朝中选职。
考虑到孙恩隐患,谢混找到谢琰,说明自己的想法:“父亲,如今海上异动频繁,我欲带兵前往句章一探究竟,还请授予我长史一职,便宜行事。”
现在谢琰都督着八郡军事,军府长史可代为行使军权。
如今,广武将军桓宝、谘议参军刘宣之等人,分别镇守在句章、上虞。
职位低了,可压不住这些人。
谢琰自无不可,当即授予印信。
“要不我与你同去?亦或是你再多带两千人?”
谢琰有些不放心,担心谢混出什么意外,那句章临近海岸,要是贼寇来犯,必定首当其冲。
“不用,现带两千人足矣。况且桓将军杀敌英勇,孩儿很是佩服,我不会胡乱指挥。”
几个月前桓宝领前锋,直插孙恩叛军的场景,谢混还历历在目,确实令他比较欣赏,只可惜,这人出自桓氏。
未来,他是必定会与桓氏为敌的。
思及招兵、安抚士族等事宜,他又特意叮嘱谢琰:“父亲,当前最重要的是募集流民,以及颁布仁政,与当地士族打好关系,扶植亲信。”
谢琰昨日便想通了,自然不会反驳:“行了,为父稍后便着手安排。你去了句章,万事小心,事不可为就退回会稽。”
...
会稽到句章约两百里,途经上虞。
谢混领着蒯恩一行人,到上虞后,稍作修整,再婉拒了刘宣之的宴请,又直接奔赴句章。
此时。
临近句章海岛上。
“孙仙师,这是给您带的粟米。沿岸句章、上虞的万余信众,都盼望您杀回去。还有一些士族,也暗地里传信,说可以引路。您看?”
一名信徒将手中陶罐放下,眼神狂热。
孙恩虚眯着瞄了一眼,见罐壁上有少许血迹,心中透亮,砸巴两下嘴,说道:“本仙师正有此打算。”
近月以来,他一直在安排岛上信徒准备船只、武器、攻城器械,既然岸上有人接应,正中下怀。
边上的卢循,听到有吃食,立即上前抓起罐子,伸手掏出几把粟米,仔细看了看。
检查确认没问题,这才扔进旁边沸水中。
徐道覆皱着眉,思索片刻后,给出提议:“灵秀,几月前那谢琰水陆夹击攻破我等,随后又派人,一直驻守在句章、上虞。不若我们暂避这两地,换个方向上岸?”
“避什么避,依我看,就在句章上岸。此前那句章太守,修筑渎垒,还不是照样被我们杀穿。”
正盯着水中粟米的卢循,抬头大声反驳。
之前在南湖水上,他被官军水军追着杀,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小命,自然想一雪前耻。
徐道覆也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询问信徒:“有无暗道可通句章城内?”
信徒回想了一会儿,摇摇头:“回徐仙师,并无暗道。不过您若有需要,可以挖!”
闻言,孙恩来了精神,当即命令:“道覆,你即刻去通知岛上的人,做好准备。”
随后一指那送粟米的信徒,对卢循吩咐:“你带着此人,先去句章城挖几条暗道,挖好后,再去联络沿岸信徒。”
“三日后,攻打句章!”
...
句章郡府。
广武将军桓宝翻看着最近的密报,这些都是探子在沿岸,打探到的军情。
讯息杂乱无比。
其中一条,引起他的特别关注——近日,句章刘氏、谭氏,上虞陈氏、萧氏、胡氏,疑暗中聚众。
“袁大人,这条密报,你怎么看?”
他将纸条递给吴郡太守袁崧。
因孙恩就在几十里外群岛上,前句章太守被杀后,无人敢来补缺。
袁崧被谢琰指派,与桓宝一同镇守句章。
属于赶鸭子上架。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自然要守好,不然城破,便是人亡。
袁崧接过查看后,一脸凝重。
“兹以为,此为勾连的同党,孙贼近日便会登岸来犯。句章这边,应尽快命人,将这些士族控制住。同时,派人去通知上虞。”
桓宝也是这样想的,当即下令:“来人,立即通知督邮陈昌,去将刘氏、谭氏抓起来。让传令兵骑快马,将此密信送去上虞刘参军处。另外,再将此事呈报谢大人,请他随时准备派兵增援!”
“是,将军!”
看着郡功曹领命离去,郡太守袁崧一言不发。
按理说,吩咐督邮该是袁崧的权力,郡功曹也应听命于他。
但对桓宝越权发令,他却当没看见。
只因他是五品郡太守,还没军权,自然不敢跟桓宝这个四品广武将军争。
“袁大人,姚江渎垒修复的怎样了?”
桓宝想起谢琰曾安排过的事,现在孙恩即将来犯,防御工事要逐一确认。
“此前被毁部分已修缮,另外我又命人加修一道,形成东、西渎垒抵御。”
如今正值十一月冬季,修好这两道垒,袁崧可花了不少心思,征调的民夫都数以千计。
“如此甚好!”
“唉!这狗娘养的孙泰,凭借符水蛊惑愚民,现在其侄孙恩,又在这三吴聚众叛乱,令我等疲于奔波,真该死啊!”
桓宝咬牙切齿。
袁崧暗自撇撇嘴,你桓氏不也在荆襄搞事,去年把殷、杨二人除去,最近又有风声传出,桓玄在磨砺兵甲,鹰视建康。
“报!将军,谢长史已至府门外。”小吏匆匆进门禀报。
谢长史?
桓宝和袁崧心头一怔,他们不记得谢琰身边有长史,莫非是新任命的?
“哪个谢长史?”
桓宝好奇询问。
作为军中将领,自然对这仅次于谢琰的军府上佐职官,更上心。
“谢氏三公子。”小吏垂首回复。
原来是他。
桓宝摸着下巴,不禁回想起半年前在会稽城门口的一幕。还有掷剑打翻张猛,救下谢琰的举动。
对这个名扬江左的谢氏子弟,他印象很深刻。
“袁大人,我们一起去迎接。”桓宝提议。
新官来任,他们自然应该去迎人。
袁崧也对这谢混感兴趣,长史虽然管不到他,但可以压住桓宝。
二人随即招呼郡府各参军、属吏,一同来到府外。
经过一番客套后,将谢混迎入府。
随后,桓宝问出心中疑惑:“谢公子,可是谢大人有什么安排?”
除此之外,他想不通谢混来句章的缘由。
“桓将军,本人受谢大人嘱托,添为军府长史,还请呼本官职务。”当着众人,谢混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他没有时间跟这些人拉扯,必须要在这些人面前,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
桓宝和袁崧心中一惊,听这口气,似乎要掌控句章。
尤其是桓宝,他有些头疼。
如今孙恩就要打来了,谢琰却派了个儿子来混资历。毕竟可没听说过这谢公子有作战经历,到时误了军情,大家都得陪葬。
他斟酌着话语:“长史勿怪,一时口误。只是贼寇不日便会来犯,你初来乍到...”
谢混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又环顾四周官吏、参军,皆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放心,本长史轻易不会插手军务,既然贼寇将至,尔等速去各司其职,严加防范。”
官吏、参军们互望一眼,踌躇片刻后,终于有人带头,三三两两离开。
“桓将军,此次我带来两千人,驻防于城外,你觉得该如何安排。”
这支军队目前交由一名参军领着,蒯恩等人协助管理。
桓宝、袁崧惊喜。
没想到谢混还领了军队来,虽然两千人不算多,但用好了,能起到一战定乾坤的作用。
...
又过了两日。
谢混与刘穆之、桓宝一起巡视城防。
“桓大人,先前你缉拿的刘氏、谭氏,可有人招供?”谢混骑马居于中间,随口问道。
果然如他很早之前猜测的,当地有士族在串联叛军。
“谢长史,那些人口风很紧,并未招供。我已命人上刑,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桓宝的上刑,是肉刑,在这关键时候,他也顾不得禁令了。
谢混并未制止。
现在不是讲仁义道德的时候,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见谢混默认桓宝行为,刘穆之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对这个主上,有了新一层认识。
又骑行一段路。
城中街巷、道边一幕,令谢混皱眉。
只见成群难民,扎堆聚集在各处。
“桓将军,再派人搭些窝棚,多找些秸秆、絮草填充,给这些难民避冬。”
如今是冬季,城外又被孙恩祸乱,这些涌入城中的难民,已无衣粮,全靠官府开仓救济。
桓宝欲言又止,这事该袁崧负责。
之前谢混没来时,所有事都是他在管,自然不会抵触,现在有人压着,肯定要分清边界。
“铛铛铛!开饭了,开饭了!”
一小吏手持锣鼓,一路边敲边吆喝。
其身后,两名小吏抬着一个大木桶,盛着稀粥。
周边的民众,迅速聚到两人身边。
“排好队!谁敢插队,乱抢,看我不抽死他!”小吏举着皮鞭,凶神恶煞。
如同乞丐的人们,这才老老实实拿着碗,分成两列。
谢混摇摇头。
底层庶民只能这样管理,讲道理他们也听不懂。
“走吧,桓将军,回府。”
他刚才也回味过来桓宝犹豫的原因,打算去找袁崧。
正当谢混扬鞭打马,准备离开时,余光却不经意间留意到奇怪一幕。
不远处,不少难民并未挤过来领粥,而是聚在一起冷眼旁观。
有几人看向他们,甚至目露凶光。
这...很不寻常...
佯装着打了个哈欠,转头避开,脑海中却在仔细回忆。
尽管那些人外面衣衫褴褛,但内里却鼓鼓的,明显穿着厚实保暖的衣服。
有部分人,还能瞥见土黄色衣角。
五斗米道的人!
谢混心中一惊。
而后不动声色招呼桓宝离开。
身边只有几名士卒,不能以身犯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