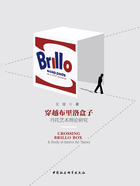
二 国外研究概况
相比国内,国外对丹托的研究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有三个批评集较为突出:一是马克·罗林斯(Mark Rollins)1993年主编的《丹托和他的批评者们》(Danto and His Critics)[20];二是著名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在1998年第37卷第4期上开辟的专栏《丹托和他的批评者们:艺术史,历史学和艺术终结之后》(Danto and His Critics: Art History,Historiography and After the End of Art);三是丹尼尔·赫维茨(Daniel Herwitz)和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2007年主编的《行动,艺术,历史:与丹托的交会》(Action,Art,History:Engagements with Danto)[21]。这三部论文集的共同之处在于,批评者对丹托作出批评后,丹托针对批评意见予以积极回应,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理论互动。
首先我们看看1993年的《丹托和他的批评者》。这部文集从四个方面对丹托展开批评:第一部分从系统论与方法论方面加以阐述。其中,丹托的得意门生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在《丹托作为一位系统论哲学家或者启发丹托的法国》(Danto as Systematic Philosopher or comme on lit Danto en francais)一文中指出三个中心问题:一是丹托深受尼采和萨特的影响,并把他们的理论转化为分析哲学的语言;二是丹托在认识论上沿袭笛卡尔的思想;三是丹托的美学属于历史编纂学。由此,他还推导出丹托的艺术理论是叙事理论,并注意到丹托的艺术哲学溢出了分析美学的范围。另外,还有沃尔海姆的《丹托的不可辨识物的画廊》(Danto's Gallery of Indiscernibles),沃尔海姆追踪了丹托的“不可辨识”思想实验,认为它只是一种假设,当遇上半成品的时候就难以清晰地对艺术品进行阐释。因此,沃尔海姆更看重艺术品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则从意图与解释方面加以阐释,其中菲戈·布兰德(Feg Brand)和迈尔斯·布兰德(Myles Brand)的《表层阐释和深层阐释》(Surface and Deep Surface)关注的是丹托在哲学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行动哲学的关系。第三部分为艺术哲学,包括迪基的《两个艺术世界的传说》(A Tale of Two Artworlds),该文中,迪基把他的“艺术惯例论”同丹托的“艺术世界”进行区分,认为丹托的艺术思想受到苏珊·朗格(Susan Langer)的象征表达的影响。另外,在这一部分中,埃诺儿·卡罗尔(Noël Carroll)[22]的《本质、表现和历史:阿瑟·丹托的艺术哲学》(Essence,Expression,and History: Arthur Danto's Philosophy of Art)是引用率非常高的一篇论文。应该说,在所有的批评者中,卡罗尔对丹托的批评时间最长,也最为丹托欣赏,他们二人在彼此回应中各自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理论。这篇论文卡罗尔从五个方面归纳出丹托早期的艺术定义,同时尖锐地指出丹托的艺术理论呈现出一种循环论证的倾向。还有,卡罗尔还注意到丹托继承黑格尔具有建构艺术史哲学的目的,这促使丹托后来写作《艺术的终结之后》来实践这一目的。应该说,卡罗尔关于丹托艺术哲学的批评不仅全面而且深刻。此外,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Soloman)和凯瑟琳·希金斯(Kathleen M.Higgins)的《原子论,艺术和阿瑟·丹托的黑格尔转向》(Atomism,Art and Arthur Danto's Hegelian Turn)一文,图绘了丹托从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原子论分析到后期黑格尔的历史语境分析的转变过程,并指出人类解释在决定历史意义上所起到的作用。第四部分聚焦历史知识,其中盖里·夏皮罗(Gary Shapiro)的《艺术及其复制品:丹托,福柯和他们的拟象》(Art and its Doubles: Danto,Foucault,and their Simulacra)一文,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示出,由于丹托和福柯的哲学指向不同的艺术史概念,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沃霍尔和波普艺术完全不同的解读。此外,还有丹尼尔·赫维茨(Daniel Herwitz)的《终结的开始:丹托论后现代主义》(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Danto on Postmodernism)和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盒中艺术》(Art in a Box)等文章。总体来说,这部论文集由英美一流学者撰写,不仅批评深刻,而且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历史主义的争论、艺术惯例论、叙事特征、后现代主义、艺术与修辞、美学与哲学等各个方面的议题,是对丹托早期到中期思想的一个全面概括,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1998年《历史与理论》杂志组织的《丹托和他的批评者》讨论,邀请了大批颇具分量的美学家加入讨论,涉及丹托艺术理论的新进展。比如卡罗尔的《艺术终结?》(The End of Art?)延续前人,继续以“循环论证”为突破口否定丹托“艺术的终结”,因而在审美上同丹托保持距离。凯利的《丹托艺术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Essentialism and Historicism in Danto's Philosophy of Art)则认为,丹托的艺术定义不能解决现代主义艺术中的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但丹托通过支持本质主义而分解了冲突。同时,凯利也意识到丹托的“艺术史哲学”所终结的不是当代艺术而是现代主义艺术,丹托通过把艺术看作过去的事情从而超越了历史的限制,最终把艺术定义的任务交给哲学。布里吉特·希尔默(Brigitte Hilmer)的《继丹托之后的黑格尔派》(Being Hegelian After Danto)表明,丹托与黑格尔的不同在于,丹托把艺术看作一个自我认识的主体,而在黑格尔眼中艺术只是辅助认知。在深入讨论后,希尔默还认为丹托的艺术定义只对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有用,所以他不赞同丹托的“艺术的终结”是一种叙事的终结。马丁·西尔的《作为表象的艺术:关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的两点评论》(Art as Appearance: Two Comments on Arthur Danto's After the End of Art),主要批评丹托的新艺术定义放弃了早期对艺术外观的注意,西尔主张外观决定了艺术品是否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另外,还有弗兰克·安克斯米特(Frank Ankersmit)的《丹托论表征,同一性和不可辨识性》(Danto on Representation,Identity and Indiscernibles)等。应该说这部论文集的特色在于,在批评者和作者良好互动的环境下,它对丹托理论的缺陷给予激烈批判。丹托后来在《艺术的终结:哲学的辩护》(The End of Art: A Philosophical Defense)一文中将问题分类,分别从艺术的定义、艺术的特质、美学、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艺术的意义、绘画的死亡、叙述句子和不可辨识问题等诸多方面作出回应。
2007年的《行动,艺术,历史:与丹托的交会》一书,批评者几乎全方位挑战丹托的哲学,丹托针对每一位挑战者做出回应。通过这种方式,读者能更好地掌握丹托的哲学。此书以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丹托的行动》(Danto's Action)一文开始,唐纳德·戴维森认为丹托是位系统论哲学家,因而丹托在行动理论中所提出的问题都能在他的美学、历史著作中得到印证。而莉迪亚·戈尔(Lydia Goehr)则把一些现实性问题与丹托的哲学相结合,比如提及社会、政治因素对丹托哲学的影响。赫维茨的《销售日期》(The Sell-by Date)则暗示丹托的艺术观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学诉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在《交叉路径》(Crossing Paths)中建议让艺术重返实用主义现象学。格雷格·霍洛维兹(Gregg Horowitz)的《图像处理,或开放艺术》(Photoshop,or,Unhanding Art)和迈克尔·凯利的论文主要聚焦当代艺术的某些现象。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丹托、历史和人类生存的悲剧》(Danto,History,and the Tragedy of Human Existence)和汉斯·贝尔廷的《现代主义的末日:竞争中的艺术和艺术理论》(At the Doom of Modernism: Art and Art Theory in Competition)则质疑哲学对历史的优先权。
除了这三个论文集之外,其他研究丹托的论文层出不穷。特别是卡罗尔,几乎跟进丹托各个时期的思想转变。表现出最大特点在于,他的辩证批判精神,即在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比如他在批评丹托的艺术定义时,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即艺术定义不仅要考虑理论、实践、叙述作为一种进步式的过程,还必须用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理论来解放艺术。另外,马修·鲍曼(Mathew Bowman)为丹托的《非自然奇观》撰写书评时指出,丹托的艺术批评并不具备其哲学宣称的特殊实践,同时反思性不够,他没有把其深思熟虑的哲学力量运用到艺术焦虑和革命等问题中去,丹托把艺术批评建立在一个长长的谱系上而放弃了对哲学的反思。最终,作为哲学家的丹托与作为艺术批评家的丹托之间出现一个鸿沟。另外,丹托的“一切皆可”也容易让他陷入多元论者的困境,并且丹托的后期艺术批评缺乏对艺术品本身——形象的关注。还有赛普尔(D.Sipple)的《阿瑟·丹托》,这是一篇综述式的论文,以述评的方式介绍了截至2000年丹托的系列创作活动。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足点是:丹托关于艺术的观点是他全部哲学思想的标志,这篇论文把哲学作为丹托艺术观点的基础,同时也涉及丹托后期的社会、政治活动,大体勾勒出丹托哲学的实践性特征。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博士学位论文也多有涉及对丹托的论述,但鲜有专人研究。2006年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史蒂芬·斯奈德(Stephen D.Snyder)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黑格尔、尼采以及丹托关于“艺术的终结”》(Hegel,Nietzsche and Danto on The End of Art),指出了丹托的“艺术的终结”指向艺术的自由实现,同时把丹托的理论与黑格尔的理论并置一起进行比较,认为丹托的理论缺乏一种交流性,史蒂芬·斯奈德主张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解决困境。2011年,斯奈德发表了《阿瑟·丹托的安迪·沃霍尔》(Arthur Danto's Andy Warhol)一文,从杜威(John Dewey)[23]的实用主义美学出发来研究丹托,并试图证明丹托与波普艺术都具有“挪用”特征。另外,在2007年贡布里希的讨论会上,史蒂芬·斯奈德指出,丹托对贡布里希的“技术性”的艺术史叙事存在某种误解。总体上,斯奈德主张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解决丹托理论与实践的断裂问题,这样,他走出了以往的研究聚焦于丹托艺术定义的窠臼,他的批判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也紧跟丹托的艺术理论的发展。较近涉及丹托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加布里埃尔·莱蒙考(Gabriel Lemkow)2011年7月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艺术的惯例论定义》(Institutional Definition of Art)。莱蒙考考察了丹托的艺术定义的发展以及“艺术的终结”观点,将之同迪基的观点进行对照,从“惯例”视野中审视艺术定义的进步与发展。
总体而言,国外研究丹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如下特点:首先,集中在哲学层面即对丹托的艺术定义和艺术哲学进行研究;其次,采纳以问题为中心的比较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对丹托的专门研究,而是附在某个主题如“艺术的终结”或者“艺术惯例论”之下进行平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把丹托的艺术哲学理论同后历史博物馆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
由于拥有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知识和对丹托资料的全面掌握,国外对丹托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具有深度。不过,比较遗憾的是,笔者目前暂时没有看到对丹托的系统研究的专著。
本书正是在上述思考与研究基础之上,考察丹托艺术理论所诞生的历史语境,进而探求其理论特征。丹托的艺术理论作为在当代西方占据主流的分析美学的重要一支,不仅有其产生的理论语境,而且他的理论也随着其关注对象——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而处于不断发展中。本书思考的理论前提是,既然丹托艺术理论的终极指向是对艺术本质的追问,那么随着商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艺术形式的急剧变化,丹托的艺术理论同样也应该具有自身的连续与断裂,具有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本书在尝试对丹托艺术理论的主要问题展开历时追踪后,试图跳出丹托自身的哲学窠臼,从文化哲学层面对丹托艺术理论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