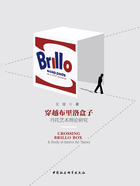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
本书作为丹托艺术理论的专门研究,有必要厘清丹托艺术理论中的几个中心问题,并试图将它们同丹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结合起来。
丹托最初从事艺术哲学写作是在20世纪60年代,恰好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期。周宪在《审美现代性批判》[24]一书中,将丹托关于艺术的观点放置到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周宪认为,由于大众媒介的崛起,曾经赋予艺术家和理论家力量的知识/权力共生结构开始衰落,于是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逐渐分离,从而产生了新的“后现代”的实践模式或观念,所以,知识分子从原来的“立法者”转变成为“阐释者”。与这种转变相对应,丹托对艺术从模仿到表现以及对波普艺术的发展轨迹的考察都是为了证明传统艺术中心和权威合法性的消失,并试图以一种商榷式的对话方式来看待当代艺术。因此,丹托赋予“艺术世界”阐释者的角色所强调的正是一种参与和对话模式,并充分重视主体的力量。这些都与丹托写作的特殊语境相关。
从丹托的理论背景来看。首先,丹托的理论立足于分析美学,他以历史哲学为指导,重点关注由历史变迁所带来的艺术概念问题。在方法论上,丹托用“不可辨识”问题和“表现说”贯穿到对艺术本质的分析。“不可辨识”问题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受启于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它让丹托提出疑问:为什么外观上一模一样的客体,沃霍尔的盒子就是艺术品,而超市里的盒子则只是普通的物品。这个问题确立了丹托艺术哲学的基本立场:知觉与艺术的联系不是必然的,并进一步发展为艺术与审美无关的观点。由此,“不可辨识”问题不仅成为丹托艺术哲学的起点,也成为他的艺术史哲学的起点。而“表现说”则直接从丹托的历史哲学中发展而来。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在借鉴尼采的主体性的历史态度后,丹托创建“叙述句子”阐明主体具有能动把握历史的能力。这个观点延伸到丹托的艺术哲学中,他提出“表现说”重视艺术品本身孕育的含义,比如艺术家的观点和相关的主题,后来被归纳为“相关性”和“具体体现”两条原则。其次,黑格尔的理论从艺术与历史的关系上给予丹托启示,即历史与艺术不再同向,历史动力与艺术动力不再重合。然而,丹托置身20世纪,他立足于当下语境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观点,所以他对黑格尔的沿用只限于艺术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的历史。
总之,对丹托的研究必须深入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他的艺术理论始终与其背景哲学相互渗透,因而呈现出本体论的特征。归纳起来,丹托艺术理论有以下几个中心问题。